几千年来,中国一直都在不断地演绎著“苛政猛于虎”的悲剧。在毛泽东统治的时代,出现了大饥荒饿死数千万农民的惨剧,而且农民还出门逃荒的最后的自由也被剥夺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由于农村改革严重滞后,激发了“三农”问题的严重性,农民收入越来越少、负担却越来越重。中国的乡级财政普遍都已破产,有的一个乡就有上亿元的财务黑洞。在此背景下,一些基层干部对农民的无情盘剥和粗暴干预便越来越厉害,“官逼民死”的现象怵目惊心。那么,逃到城市讨生活的农民情况如何呢?城市不是农民的家。领袖喜欢在“国庆”的庆典上挥手,然而就因为领袖要挥手,数十万记的民工便被警察驱逐出北京城。“我爱北京天安门”是每一个中国孩子都耳熟能详的儿歌,但一个残酷的现实却是:天安门从来都是帝王们的天安门,天安门从来不会“爱”一个农民的孩子。农民的孩子在城市中得不到受教育的机会,而那些自愿为民工的孩子提供服务的好心人,却被政府看作捣乱分子和坏人。在北师大组织“农民之子”社团的大学生徐伟,因为挚爱农民兄弟并质疑官方的农村政策,就被安全部门秘密逮捕并以“颠覆国家”的罪名判处十年徒刑。这样,谁还敢为农民说一句公道话呢?
在中国,“农民”不是“公民”,“农民”是可以被政府和高级华人们任意掠夺、欺凌和侮辱的对象。农民没有未来,他们只有过一天算一天的“无主名”的生命:他们被当作“盲流”关押在收容站以及遣送回乡的闷罐车中,他们因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被拆毁了房屋而成为流浪在他乡的“超生游击队”,他们因为没有钱去医院看病而只好在家中等待死亡,他们因为缴不起苛捐杂税而只好喝农药自杀,他们因为拿不到建筑公司的工钱而被迫跳楼他们不是不珍惜自己的生命,只是对于他们来说,此生的痛苦并不亚于死亡的恐怖。
偶尔,农民也会揭竿而起,以暴易暴。不抗争是死,抗争也是死,他们无法做出更好的选择,只好仿效两千多年以前的陈胜和吴广。据说,某党国要人到农村视察,到一农户家中,见其家徒四壁,乃故作关心状,问道:“大爷缺点什么?党和政府会很快就给你送来。”老农答曰:“我们什么都不缺,我们就缺陈胜和吴广。”老农说的是一句大实话:从被动的“民不聊生”到主动的“民不畏死”,其实只有一步之遥。
据陕西《华商报》报道,2000年八月二十日晚上,因为西安市北郊徐家堡一钢厂拖欠工人工资及一名工友被打,数百名四川籍民工群起抗争。有的手拿钢筋、有的手执木棒,聚集到工厂里,砸毁了四五间办公室,还砸坏两台电机。闻讯,西安市治安局巡特警队、西安公安局未央分局以及谭家派出所、徐家湾派出所出动大批警力赴现场制止。
劳工与资方的对峙,一直持续了整整一个通宵。到了二十一日上午,双方协商无果,矛盾再度激化。当四川籍民工得知他们当中有四人被工厂的值班人员用铁丝捆绑殴打、老板也没有答应给他们回家的路费之后,群情激愤。民工们持械将厂里的围墙砸开个大洞,冲出厂外继续闹事,场面一度失控。在有民警被打伤之后,警方鸣枪警示。当时真可谓千钧一发。十一时许,未央分局所有派出所包括特巡队前往钢厂支援,这才勉强控制了局面。下午一时许,老板和十多名带头闹事的民工被警方带回讯问。
关于冲突的起因,十余名四川民工告诉《华商报》记者:八月二十日下午五时许,一名四川籍民工唐某想不做了,要求发放七月份的工资,在与老板理论时遭到厂里的值班人员(民工称是老板雇的打手)用砖头和铁棍殴打。唐某被打得跑向车间,随后又向东翻过围墙跑,随即失去踪迹(民工们猜测是被打手们抓住关了起来)。晚上八时许,数百位民工再次来到厂里,一方面继续讨要工资,一方面寻找那名被打民工下落,但是工厂老板一直躲著不出来。随后双方发生激烈冲突以至于警方介入。
此次西安警方出动的警力,分别隶属不同的部门,拼凑起来简直就是一支小型的军队。为什么政府要出动如此庞大的警力才能控制局势呢?为什么警察要把枪口对准手中只有“冷兵器”的农民呢?在这两个问题的背后,其实还有更加深层次的疑问:一向纯朴老实的民工,为何要拿起武器来抗争?一向胆小怯懦的民工,为何突然间变得毫不畏惧死亡?
由此事件可以看出,首先是“民不聊生”,接著才是“民不惧死”。这个制度已经蜕化成一种不让人好好活著的制度了。农民们失去了“活著”的希望,便不得不挑战这种邪恶的制度,尽管农民的挑战通常不会有好的结果,反倒会导致更加悲惨的命运。但是,他们还是孤注一掷,我能想象他们蜷缩在工棚之中时的绝望、无奈和痛苦。他们知道没有任何一个政府部门或者民间机构能给他们“主持公道”,在中央和地方的各级官僚中也不可能出现一个“包青天”式的人物。哀莫大于心死。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中国的“三农”问题似乎进入了一个死胡同。那么,还有没有解决的方法呢?《南方窗》杂志在一篇题为《给农民以宪法关怀》的社论中提出:“历史和现实已经证明,只要给农民自由,农民就会创造出惊人的历史奇迹。现在是进一步解放农民的时候了。这就迫切需要我们虔诚地恭请神圣的宪法之母从幕后走向台前。理性在召唤我们,赋予农民以真正的宪法关怀,是解放农民的终极选择。宪法是保障人民基本权利的最神圣的法律,没有宪法就没有共和国。宪法的根本功能在于:一方面约束政府易于膨胀的权力,一方面慈祥地保护人民易于受害的权利。在宪法之母的眼中,没有权贵和贱民,也没有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区分;在宪法之母眼中,只有平等的公民概念,任何人都是慈祥的宪法之母的高贵之子。”让宪法真正成为农民的“保护伞”,看起来似乎是一种好的解决之路。只是,我认为文章的作者未免过于天真了:那些长期骑在农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官僚,会自愿放弃他们的权柄而给予农民充分的自由吗?而早被独裁者们玩弄得遍体鳞伤的中国的宪法,还能够发出“宪法之母”的光芒来吗?
2003年八月二十六日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居北京
摘自《观察》(原题为《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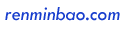






























 打印机版
打印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