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下午5点多钟,我草草地吃了点东西,带上事先准备好的纱布、口罩、遮阳帽,和爱人交待了几句,便骑上自行车,直奔西长安街走向最危险、最需要民运人士的地方。
大约在傍晚6点15分左右,我投入了在军事□物馆西侧300米处、市民们阻挡西线前来戒严的解放军车队(以下简称车队)的战斗。车队的前面是上百名身穿迷彩服的“防暴”士兵在开路,后面是望不到尽头的戒严车队。战车上的士兵枪口向外,不许任何人接近。“防暴”士兵手持盾牌和石头,有秩序地不断攻击前方的市民。由于他们训练有素,投出的石块既远又命中率高,随着一块块石头的落下,有几个市民的头被打破,流出血来。我们这些手无寸铁的市民面对武装到牙齿的“防暴”士兵和战车不得不逐渐向后退却。
为了将西线的军车完全阻挡住,占据主动形势,我与5、6位男青年在现场充当起了“指挥员”的角色。我们将3、400名前来堵军车的市民召集在一起,向大家讲述了我们的想法和行动计划:第一,这种局面相持下去对我们很不利,我们必须扭转这种局面;第二,我们的目的是走在军车跟前与士兵们对话,市民见到我们走到军队跟前没有危险,大街两侧的市民就会源源不断地走出来支援我们,那时,我们就会用人流将军车拦截成几段,把他们彻底阻挡住;第三,我们排好队伍打起标语,有秩序地走过去,我们不要扔石头,大兵向我们扔石头,我们也要忍住,只要我们走到他们跟前,我们就胜利了。北京市民的政治素质就是高。整个工作安排只在10分内钟之内就完成了。3、400名男女市民自动排好队伍,打起标语,呼喊着对话口号,有秩序地走向军车。“防暴”士兵被我们的阵势搞得不知所措。他们都不由自主地回过头去,看着一位带眼镜、穿制服的军官。
我们的队伍与“防暴”士兵的距离越来越近了,从开始的200多米,变成了20米、10几米。我看到他们的指挥官把手挥动了一下,不知喊了一句什么命令,上百名“防暴”士兵一齐向我们猛烈投掷石头。
霎时间,我们走在前排的市民几乎全被士兵掷来的石头击中。我的肩部被石头重重地击了一下(打出了血印子)。身边的某某中学初三的王同学(后来才知道他的身份;以下简称小王)的额头被砸破,血流满面。
由于我们这支队伍是群众临时聚成没有应付经验,在士兵的野蛮攻击下,大部份人从地上检起石头进行反击。其实这正中了军队的“激将法”。假如我们不还击,继续挺进到士兵近前,就能实现阻挡这队军车的计划。可是在双方对掷石头的情况下,群众根本不是训练有素的士兵的对手。虽然我们几位“指挥员”还想挽回局面,但毕竟大势已去。我们只得护送着伤者撤退到路面的两侧。
在“防暴”士兵越来越多、越打越疯狂的势头下,我们这些手无寸铁的市民只得边抵抗、边彻退。在军事博物馆东侧路北的一台压路机的旁边,我再次与头部受伤的小王相遇。我用随身携带的纱布换取下小王伤口上的手绢。只见小王的灰色短袖上衣已被鲜血染红了一大片。由于责任感,我将一手捂纱布、一手向士兵扔石头的小王拉近了路边不太远的居民区。由于这个居民区出入口处的门诊部关着门,我俩只得在热心的市民指引下,在居民区的东北处找到了一个医务室。在这段时间小王告诉了我他的身份,并表示包扎好伤口还要去抗击军车。女医生给小王包扎好伤口后没有收取我们任何费用,只是和市民们一样不停地骂共产党的军队是土匪。在我们往回走的路上,街上连续不断地响起了枪声,时间是傍晚6时40分。
当我们走回到居民区出入口的门诊部(位于第二层楼上;此时已经开门)时,见4名男青年抬着一个女青年大喊着“让开、让开”,朝这里快速奔来。在抬伤者上楼的时候,我也加入到救护行列。当我们把女青年放在诊疗室的地上时(屋内已有两位伤者躺在仅有的两张床上),女青年的脸色刷白。她的乳房已被罪恶的子弹打烂了。胸部血肉模糊,惨不忍睹。靠西侧病床躺着一位脖子被罪恶的子弹击穿的男士。东侧病床上是一位在大腿上被罪恶的子弹击中的男青年。在我下楼的时候,又有一位男青年被抬了上来。
从军事博物馆西侧300米处到木樨地大桥,由于遭到北京市民自发的、英勇的抵抗,中共的军车爬行了50分钟才通过这几百米长的路段(在木樨地大桥到西单路口的这段路上,军车遭遇到了北京市民更加顽强的奋力抵抗)。
在木樨地大桥上,军车由于受到路障的阻拦,士兵发疯似的向路北开枪。我与数千名市民被迫蹲在地上。唯一回敬他们的办法是用自己的声音来呐喊。几千名市民有节奏地向军车方向喊出两个字:土匪、土匪、。
在这一夜的西长安街上,曾经号称人民子弟兵的解放军,变成了人人憎恨的土匪。在他们的枪口下,数不清的男女老少倒在了血泊之中。
这一夜充满血腥的画卷,10年来始终不断地在我脑海里浮现……
(1999年4月 清明节)
(中国社会民主党论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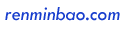























 打印机版
打印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