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的手,是释放母爱光辉的手。“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唐代大诗人李商隐把这东方式古典母爱的内敛和蕴藉,经过这种意象描写,可以通透所有善良人的灵犀。米勒笔下的母爱,他总是把艺术视觉的焦点凝聚在女人的手上。夕辉里“晚祷”的手,打毛线的手,缝衣服的手,通过形神的专注、心的跳动和手的灵动达到了完善的统一,我们领略了母爱光晖的庇佑。
女人的手,中国古典母性爱子于严中。昔孟母断机杼的手,那种决绝,断然和“三迁”,她以东方母爱的巨擘大手,成就了一个与孔子齐名的东方智者。比这更为之视野广大的,是岳母把她的大爱融入和注进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大运里,她以自己给予的血,以感同身受的刺骨疼痛,用血的语言在英雄儿子的脊背上,把“精忠报国”的民族宏愿嘱托。从此我们知道什么叫“疼爱”。
女人的手,是执干戈以卫社稷的手。少女花木兰父亲年迈,当边关吃紧,军帖下达,她在“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的家境下,再也坐不住“当户织”的织布机上了。她瞒过了募兵人,以女扮男装的身影代父从军。她的纤手不但能灵巧地拉动织布机上的梭子穿动不息,使棉丝成布成帛,她的纤手亦可举银枪、跨骏马,“关山任飞度”,“耳听黄河之水鸣溅溅”。她同男人一起,并胜过众多男人,变女人的诸多不能为全能,驰骋疆场,御敌国门,为巾帼之人抒发了一腔气吞长虹的豪情壮怀。
女人的手,是巧夺天工的手。如果说扶犁耕田不是女人的长项,那么拿起绣花针刺绣则为男人所望尘莫及。名扬四海的中国湘绣、苏绣,特别是其中的“双面绣”,立体、透视、摇曳多姿,置于户外,那花朵的艳丽可招蜂引蝶,可谓妙手回春。今天我们在世界舞台上有幸观瞻到美国神韵艺术团的演出,那斑阑多彩精致的服装剪裁和制作,似应出在天上神灵之手。
女人的手,是能制造美妙旋律,绘出声和色的手。这声音在很早的唐代就响在了浔阳江头的夜晚。白居易的《琵琶行》中那操琵琶的女手,能使“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闲关莺语花底滑,
幽咽泉流水下滩。水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渐歇。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东船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如果说白诗人借琵琶女的手绘声绘色的说出了人间不幸事,为自己被贬谪的抒怨,那么神韵艺术团诸位女演奏家如戚小春的二胡之音,则是对天簌之音的置幻,极富浸润力地对观众心灵的注入。
女人的手,是会说话的手。这里说的不是发声,是表达。手动为舞,足动为蹈。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是人的情感,由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嗟叹——咏歌——到手舞足蹈的极致。那千变万化的手舞,从细腻亲切的委婉诉说,到忧焚难耐的痛苦撕裂,由痛断肝肠到天逆地裂,从揽月摘星的高渺,到细针密缕的穿针引线,所有舞蹈语汇的联袂,她们的纤手则无所不能,无所而不能不达于惟妙惟肖,充满生命活力的淋漓尽致。
全部人类文明史,特别是东方神传文化的文明史的养成,神州大地的女人,皆以淑贤、慧能、典雅、娴静、安谧、窈窕著称于世。她们的纤手举止,都是受惠于善的派生。
然而,时代变了,女人的手也变了,这不是由观察所得,而是火辣辣地给予。自从红朝红司令掀起了红潮浊浪,似乎天下女青年的手都从文质彬彬换成了“要武”的。宋要武带着她的要武队员,亲手以棍棒和皮带打死北师大附中女校长卞仲耘;女造反派头头谭厚兰和她的一群女伴同男的一起,拉倒了孔子塑像,砸碎了康熙手书的《万世师表》、《斯文在兹》的匾额,掘了孔子墓及其世孙——明剧作家《桃花扇》作者孔尚任的墓,曝骨于林中草丛。
那时,本人的身分是“五类”末位之人,俗名称“死老虎”。被当作不是人的人。我虽然不是教师,却身处一群女孩子包围之中。红潮涌来之前,她们身上尚葆有着女性的一些美好基因,也听惯了她们口喊的“老师”声。“运动”了,她们就开始拿我“练胆”了,譬如瞪眼、呵斥、命令“右边走”、罚站、低头、弯腰、挂黑牌,唱自己编的不成调的《我是牛鬼蛇神》歌,极尽羞辱之能事。
对于挨打,我是有思想准备的。因为那时是遍于国中的一种“时尚”。那天,在一次批斗我的会上,一个女孩子箭步跳到我跟前,(因我身高)跳着打了一巴掌。我顿觉眼冒金光。接着就是火辣辣生疼。一次,就一个女孩子打,就一掴。当时曾一度阿Q地想,我比同类人,甚至不入“类”的“臭老九”,是不幸中的万幸了。接着,我心惊胆战的意识到:我们整个民族下一代的下一代,女人的手……打我耳光的那女孩的手,那么纤细修长、竹笋般白皙柔美,是不是还能拉扒大一个善良的女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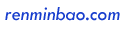

































 打印机版
打印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