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壯實的山西大個子不屑一顧地對我說說:「六四的時候你在哪?你不過在上初中。我可是參加遊行的。戒嚴令一下大家都鳥獸散了,那些留在天安門的都是別有用心。」好一個別有用心!我默不作聲。當年滿清入關的時候,剃髮令下來的時候,中國男人紛紛反抗。韃子要動手殺人了,大部分人順從了,寧死不屈的人被砍了腦袋。難道那些興高采烈地刮光了腦門留豬尾巴的膽小鬼會恬不知恥地拍着自己的胸脯說:「看,所有人都剃頭了,你們爲什麼不肯剃呢?不肯剃髮肯定是別有用心。」我實在不能理解這別有用心四個字到底是什麼意思。大凡太監並不憤恨閹割他們的人,相反卻看那些有男性特徵的人看不順眼,目之爲異類,總覺得天底下的男人都像他們一樣才是正常,否則就該殺。
旁邊一個年長些的湖北男人說:「別爭了,當時我在北京。北京到處都是垃圾,簡直搞得像垃圾場,公交車也不通了,這樣下去怎麼得了。」旁邊一個女人用尖聲尖氣的上海腔跟着說:「你以爲,那些學生真愛國,瞎起鬨。不用上課,吃飯也不用掏錢,坐火車不掏錢。什麼募捐啊,北京市民捐了那麼多錢,不多塞到自己腰包裏去了嗎。還有啊,你以爲他們是真絕食啊,說是絕食,還不是自己偷偷吃東西」。看她繪聲繪色的樣子,我忍不住想,如果她當年如果參加了絕食,一定是她自己描繪的這個樣子。我真不明白在很多人的心中,同胞的鮮血和生命竟然抵不上垃圾,免費快餐和公交車票。正是這些市儈的人無時無刻不忘記用自己市儈的眼光去看看歷史看別人,彷彿這個世界上除了和他們一樣市儈的人就沒有人了,就不曾有過人了。
印象中六四的時候,遊行的學生還是相當有紀律的,學生組織有自己的糾察隊。直到當局戒嚴之前,前後十多天一直井然有序,並沒有混亂的局面產生。遊行示威難免會影響市容,阻塞交通。美國西雅圖舉行世貿會議時候街頭比六四時候的天安門混亂高百倍,卻沒見美帝國主義政府開坦克車去鎮壓。遊行示威,事出有因,又不是尋恤滋事,當然是政府讓羣衆不滿在先,老百姓對貪污腐敗已經忍無可忍,當時絕大部分人是同情學生的。如果要追究影響市容,阻塞交通,咎也在中共。如果中共能與學生達成妥協,給全國人民一個滿意的答覆,天安門的狀況當然不會持續下去。學生也是人,當然會有這樣或那樣的毛病,遊行的隊伍參差不齊,有幾個渾水摸魚的人也在所難免。問題是遊行本身理由是不是正當,要求反貪污反腐敗是不是正當。人和事物有的有善和惡之分,有的有對和錯之分,還有的分不出對和錯。少數學生的行爲只是缺憾和瑕疵,而中共屠夫脫下僅存的畫皮露出猙獰的面目,動用坦克大炮對準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那是赤裸裸的邪惡。拿着放大鏡在屠殺後的屍體上找斑點爲屠殺辯護本身就是狼對羊的混帳邏輯。所有的人都有缺點,這並不構成都我們都應該被石頭砸死的理由。如果這樣的話,那麼所有的殺人惡魔的行爲都是正當的。希特勒會說:「你們應該爲我消滅猶太人歡呼,誰敢保證我殺死的猶太人中沒有一個小偷呢」。
當然被垢坻最多是六四時的學生領袖。一個年紀輕的北京學生說:「我覺得絕食的學生很傻,完全是被利用的工具。那些學生領袖爲什麼不絕食,一鎮壓一個個都跑到美國去了。還有那個叫XX的,說什麼,不流血不足以引起世人的注意,她爲什麼不流血。」
誠然,一些學生領袖的種種表現,很多地方的確讓我們失望,我在這裏並不想完全袒護他們。但是一些邏輯混亂,譁衆取寵式的侮辱謾罵,聽起來非常荒謬可笑。通過謾罵這些學生領袖,進而否定六四,詆譭被屠殺的學生和市民,說他們愚蠢不值得同情,這種邏輯就更叫人啼笑皆非了。六四起因我不想贅述。
中共暴政,貪污腐敗,民怨沸騰,要求政治改革,學生激於義憤,走上街頭。屠城之後,中共血口噴人,玩弄一貫伎倆,給學生和市民扣上一頂被國內外反華勢力利用的帽子。既然是學生運動,當然就有學生組織者,並不存在誰被誰利用的問題。滿腔熱血的學生對中共兇殘的面目不甚了解。當時有誰會想到「人民政府」會大炮機槍對準手無寸鐵的學生呢?一些所謂學生領袖的種種口誤有情可原。絕食只是學生隊伍中的一部分,當然不可能所有的組織者都去絕食,我想也會有組織者在其中。至於中共開槍屠城,本來就是始料未及,求生是人的本能,怎麼能對那些學生領袖苛責,要他們都去做譚嗣同呢。如果不滿中共的人都作了譚嗣同,中國人剩下都是軟骨頭,中共專制不就是萬世一統,垂之永遠了嗎?
至於有些人逃出美國,進了某某大學,那也是以後的事,是事情的結果。如果說他們是爲了到美國才組織遊行,把同學送到中共的槍口,彷彿屠夫不是中共而是這些學生領袖,這純粹是顛倒前因後果,混淆視聽,是潑婦罵街的把式。不敢去斥責雙手沾滿鮮血的劊子手,不敢去同情被屠殺的無辜者,反而裝腔作勢地辱罵仇恨沒有被劊子手殺死的人,分明是幫兇的嘴臉。彷彿要劊子手把所有和他們不一樣的人,所有不願做幫兇的人統統殺光一個不漏,他們才拍手稱快。
那些所謂的學生領袖同樣是普通的人,同樣是中共專制教育下成長的,也會良莠不齊,也會有種種缺點甚至難以原諒的過錯。但是他們只是六四的一部分,不是全部。中國的民主不只是他們的事,也在我們每一個熱血青年的肩上。瞧瞧這羣是非不辨,善惡不分,助紂爲虐,替中共狂吠不已的精英同胞們,難道我們就只會只需要對這些學生領袖,被共黨迫害的家破人亡的人無休止的指責謾罵嗎?首先要明白最起碼的善惡,仇恨那些殘暴無恥的劊子手。一個最起碼的善惡都不分的人不配叫做人,更不配對他人侮辱謾罵。
這時候一個消瘦長脖子的陝西女生憤憤的對我說:「既然殺人是邪惡,那學生市民殺死解放軍是不是邪惡,燒搶軍車是不是邪惡?如果不制止,共產黨就要倒臺,要是我,我也會開槍。」看着她兩眼冒着兇光,不禁覺得毛骨悚然。戒嚴之前並沒有打砸搶。身強力壯的士兵開着坦克,架着機槍往天安門廣場開,明知道一路上都是遊行的羣衆,難道還好無恥地栽贓,是學生市民先搶了槍,然後開的槍嗎。這就好比在人山人海的公園裏埋上地雷,然後說是遊人自己踩的。
我對這位長脖子女生說:「如果一個手持兇器的壯漢殺死了一個弱小的嬰兒,然後說是正當防衛,你說這可笑嗎?」「如果那個嬰兒真的威脅他的生命呢」那個女生不假思索地辯解道。我看着她那張毫無血色的臉,也不再做聲了。是啊,在獨裁流氓的喉舌媒體的宣傳中,從來都是黑白顛倒了,柔弱無力的嬰兒爲什麼不能成爲殺人犯呢,而凶神惡煞的屠夫爲什麼不能是導師大慈大悲的救世;當屠夫殺人之後,爲什麼不可以理直氣壯地說「爲什麼殺他,因爲他的腦袋把我的刀磕出了豁口!」然而,令我不能明白的是,爲什麼總有那麼多高智商的精英們樂意不假思索的鸚鵡學舌呢。那些自以爲聰明的人啊,當你們爲屠戮者做咄咄逼人的辯護的時候,你們如何面對去死在地下的冤魂,你們的手上是否也沾染了的被虐殺者的鮮血。
又到了六四,人們總是希望把它忘得越乾淨越好。雖然我對同胞們的殘忍和冷漠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而往往我再次睜眼看到的殘忍和冷漠又讓我心酸、心涼、心痛。坦克碾過的年輕的軀體在他們眼裏不過是風吹過的草芥;累累冤魂在他們心裏不過是遙遠的傳說;無辜者的獻血遠抵不上那個邪惡政權在鯨吞蠶食,敲骨吸髓之餘曾經給過他們的一星點牙惠,死難者親人的眼淚和傷痛遠抵不上他們所關心的那個獨裁政權在外國人眼裏的面子。爲了這一點點既得利益,爲了一點點所謂的面子,他們可以不顧善惡良知,可以傳播謊言,可以無視自己被奴役被屠戮的同胞的苦難和冤屈,然後把自己的所作所爲恬不知恥的標榜爲愛國。這就是我的同胞!
我的心一次次被觸痛,我已經出離憤怒,我已經無話可說,因爲我不知道再一次提起,又會因此引發多少稀奇古怪的歪論。我知道,同胞們,也許你曾經是或者還是一名黨員,不想在外人的眼裏被目爲和屠殺者同儕;也許你國內的親人明天還要交思想彙報;也許你的親人明天辦護照還要出具什麼證明還要看看大小官吏的顏色;也許你在盤算着你國內的朋友親人爲你牟取的一個位置。所以,親愛的同胞們,我不想要求你們太多。我只想說,只在今年六四的夜晚,忘記這所有的利益和立場,把手按住自己的胸口,認真看一眼自己的良心,不要和我辯論,讓我們一起爲十三年前死難者和他們的親人們祈禱。
謹以此獻給六四的死難者。
蕭寒 2002年5月19日於多倫多
摘自(博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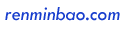





















 打印機版
打印機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