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她用一雙蒼老的手撫摩汽車的樣子,聽她沒牙的口中說出的話在風中飄飛,我淚流不止,在她行將走完這漫漫的一生的時候,她才「有幸」看到了什麼是汽車!這就是我們勤勞善良的祖輩的命運嗎?電視記錄篇說開通這條山路用了幾十萬元錢,山路沒開通以前,村民們每每出一次大山都像是出一次遠門一樣,他們要用肩膀翻山越嶺地把自家山坳裏生長的土特產品背到山外去賣,那種艱辛,我相信自己是無法用語言表達出來的。可是,就在那個通車儀式上,卻有那麼多的高級轎車,一排排地亮在那裏,其實,用那些車裏面隨便的哪一輛都能換來這條路的。
看完電視以後,我都不明白這個電視記錄片所要表達的東西是什麼,是說那些山民們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終於」有了一條可以下山的路麼?是表揚黨和政府的功績,還是爲了讓我們看看那些人是生活在怎樣的艱辛裏?已經有多少次了,每當我們的老百姓遭受到災難的時候,我們從媒體中能夠看到什麼?我們能夠從中得知誰該對這災難負責的麼,我們能夠聽到老百姓對責任人的批評麼?不能,我們所能看到的是我們的媒體怎麼樣把一次次的災難轉化成一種歌頌的。抗洪搶險如此,抗震救災如此;發生海難時如此,發生火災的時候,還是如此;老百姓貧窮了多少多少年,貧窮到了沒見過汽車、不知道什麼是電視,從來沒有走過柏油馬路的時候,還是如此──當有一條山路的時候,總是歌頌著什麼什麼「關懷」之類的,有誰想過這「關懷」是不是來得太晚了點,有誰想過要對這晚來的「關懷」提出一點質疑?當然,我們都知道,發出質疑的聲音比歌頌是困難得多的,也好像危險得多。表面上看,另類,總是不被接受的。但是,如果我們能從歷史的漫漫長途來看,還真說不好,到底那一種才是另類呢。
誰對得起中國?
「大躍進」搞得最如火如荼的1959年,爲了標榜自己「高舉三面紅旗」的政績,以路憲問爲首的河南信陽地區領導班子中的9個常委有8個同意把全地區的糧食總產數量由10多億公斤浮誇成35億多公斤,爲了實現這個謊言,他們以這個數字強行向農民徵糧,徵不夠,就開展「反瞞產運動」,直至讓農民家裏顆粒無存。到了1960年的所謂「三年自然災害」期間,雖然在河南的信陽地區的官倉裏堆滿了糧食,但是,爲了不讓上級知道自己曾經有過的強徵糧食的罪行,路憲文他們硬是眼睜睜地看著本地區100多萬的老百姓成了餓殍,許多人家的房屋都成空房,有的地方,人餓死了以後都沒有活人去埋了!100多萬條生命,就這樣白白地死了,他們死得有多冤誰又能知道呢?
而那100多萬人並不是一下子就成了餓殍的,在他們從捱餓到死亡的期間是有一段過程的,在這個過程中,饑民們爲了生存遍食野菜,而路憲文一夥爲了怕饑民給自己的「政績」抹黑,竟然派人去砸農民的鍋,就連農民外去討飯這條路,也被那些禽獸不如的暴虐幹部攔路設卡給擋住了(以上資料來自網絡上的新聞組)。
連討飯都不允許,這樣的日子在中國幾千年的封建歷史時期又曾見過幾回?而現在,當人們想反思過去,追問在「三年自然災害時期」到底餓死了多少人,都成了一種禁忌,爲什麼?早在多年前就已經有人對「自然災害」這一說法提出了質疑,可是,這樣的聲音也成了一種禁忌。
誰對得起中國?
遇羅克在1966年寫的《出身論》裏,列舉當權者殘害「黑五類」(地主、富農、反革命份子、壞份子、右派份子)及其子女的手段,有過「殘酷的『連根拔』」一句,指的就是發生在1966年8月的慘絕人寰的大興縣屠殺事件。
1966年8月26日,大興縣公安系統傳達了公安部長謝富治的講話,從8月27日至9月1日,這個縣內的13個公社、48個大隊,先後殺害了325個「黑五類分子」,最大的80歲,最小的才38天,有22戶人家被殺絕。(見《「文化大革命」十年史》1986年9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大興縣有十三個公社進行了屠殺,最有名的是大辛莊公社。
中心大隊的貧協主席,一人用鍘刀鍘了十六個人,自己也緊張得癱倒了。鍘死的人都塞進一口深井裏,直到井快塞滿了。黎明大隊把殺死的人埋在村北的一片葦塘裏。後來,乾脆把活人就往葦塘拖,用繩子套在脖子上,連拖帶勒,到了葦塘人也就斷氣了。
靠近公社的大隊,好幾個都把「黑五類」殺絕了(據遇羅文的文章《大興屠殺調查》)。
誰對得起中國?
每當我想到這個問句的時候,我都不能忘記自己在日常生活中所受到的一次又一次的刺激,刺激我的東西有很多,而且,那些東西也會隨著時間的流逝而被忘卻的,就像魯迅先生所說,「時間永是流逝,街市依舊太平,有限的幾個生命……」,巧的是,我有時候會把自己所受的刺激「記錄在案」──
2001年5月16日,從網易電子雜誌《新聞綜覽》上看到了《貧困學生丟了十元錢全班學生投票選"賊"》,原文如下(有刪節,但無改動):
兩嶺鄉九年制學校位於陝西省山陽縣一個偏遠的山村,這裏山連著山。席飛是兩嶺鄉九年制學校初一(1)班的學生,對於無爹無孃的席飛而言,10元錢是他在校生活半個月的「口糧」。
席飛家境貧寒,3歲時母親突然患病離家出走,後來聽說殞命他鄉。從此,席飛便與多病的父親及爺爺奶奶一起生活。然而,天有不測風雲,席飛12歲那年,父親也染病身亡,剩下他和年邁多病的爺爺奶奶相依爲命,經濟上主要靠在縣城工作的叔叔和20歲就出嫁了的姐姐的接濟。
4月中旬,住校的席飛要在學校買飯票,卻實在難以啓齒向爺爺要錢。他便趁爺爺不注意,悄悄把家中的8公斤黃豆種子拿出去賣了15元錢。除了買部分學習用品外,席飛把剩下的10元錢放在上衣兜裏,準備到學校買飯票。
4月17日上午下課之後,席飛到操場打乒乓球前把上衣脫了放在課桌裏,當時他還摸了摸兜裏的錢。打完乒乓球后,他一直沒有穿上衣,下午下課後,又到離學校不遠的河灘上看書,直到天快黑時才回到教室。當他拿出放在課桌裏的衣服時,發現兜裏的錢不見了!他當時嚇壞了,這可是準備買飯票的錢啊!沒了10元錢,半個月的伙食怎麼辦?他又找了幾遍,還是沒有見到錢的影子,只好將丟錢的事告訴了班長和同學們。
班長李松柏知道情況後,立即在班上宣佈了此事,並發動全班同學查找,但最終未果。李松柏只好將此事告訴了班主任朱耀貴。朱老師趕到教室後說,誰拿了席飛同學的錢,課後可以交到老師那裏或悄悄還給席飛同學,這樣就可以不追究責任。否則,如果讓老師查出來,就要嚴肅處理。可是直到下晚自習時也沒人承認。
找不到錢,李松柏也很著急,晚自習後,他找到朱老師,建議第二天早自習時在班上無記名投票把「賊」選出來;同時將在班上查找時發現的劉、吳兩同學臉紅的「疑點」彙報給老師。朱老師同意了李松柏的這一想法。
4月18日早自習課上,朱老師宣佈:爲幫席飛同學找到錢,現在開始進行無記名投票選「賊」。除丟錢的席飛和一位請假的同學之外,班上的38名學生將各自寫好的選票交到老師手裏。朱老師大概翻看了一下選票情況,當衆宣佈了選「賊」結果。就這樣,劉金滿和吳力鵬兩名同學被選爲「賊」,並被叫到了講臺前。
站上講臺,吳力鵬眼淚奪眶而出,劉金滿則氣憤地同朱老師爭辯起來:「有什麼證據證明我是賊?」
……
記者:「你爲什麼想出了這個辦法?」
班長李松柏:「席飛同學很可憐,想幫他找到丟的錢。」
記者:「這個辦法能找到賊嗎?」
班長:「我也不知道。」
……
2001年5月17日在萬千新聞的「熱點話題」上看到了《中國鉅貪們澳門億元豪賭紀實》一文,原文如下(有刪節,但無改動):
以下人員是在過去兩年裏,曾在澳門賭場豪賭的數十名高級別官員或國企領導中的一部分,他們所輸錢額少則幾百萬,多則上億。
朱承嶺原浙江省供銷社主任
葉德範原杭州市副市長
謝建卓原江門市城區政府辦公室副主任
魏光前原蘭州連城鋁廠廠長
謝鶴亭原廣東省食品企業集團公司總經理
馬向東原瀋陽市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
李經芳原瀋陽市財政局局長
寧先傑原瀋陽市建委主任
吳學智原十堰市某汽車貿易公司經理
張俊夫原雲南五菱汽車銷售有限責任公司經理
周長青原西安市機電設備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金鑑培原湖北省駐港宜豐公司總經理
郭剛林原湖北省仙桃市經濟電視臺臺長
岑煥仍原恩平市江洲鎮鎮長
吳彪原寧波發展信託投資公司總經理
……
這些貪官在揮霍國家財產的時候,比拿家裏的錢還方便即使是原恩平市江洲鎮鎮長岑煥仍,雖然級別不高,但身兼鎮經濟發展總公司、鎮出口物資公司等4個公司的法人代表,其調動資源的能力同樣不可小視。他能以4個公司法人代表的身分,"借"款1179萬元,以鎮長身分"借"款777萬多元,個人"調動"資金1957萬多元,全部匯到澳門賭博,輸得分文不剩。
周長青形容他在公司裏的地位時,認爲"我在公司說一不二,我說什麼就是什麼".每次他都是讓財務把錢從西安以往來款名義匯往珠海一公司,再轉到澳門。當機電公司的5000多萬公款被他"說一不二"地送進賭場,已無款可貪後,他坦承:"說良心話,如果我單位還有錢,我還會繼續再賭下去。"
……
2001年5月18日在《中新社》上看到了《瑞金教委教研室集體貪污案:盤剝學生50萬元》一文(原文如下,無刪節也無改動):
中新網南昌5月18日消息:江西瑞金市檢察院近日偵查終結的該市教委教研室集體貪污案,使這起盤剝學生試卷費的案件露出水面。這起集體貪污案涉案人員達11人,涉案金額50餘萬元。
據江西日報報道,1996年,當時就已任瑞金市教委教研室主任的鐘某,開始負責全市中小學生試卷的印刷業務。他瞄準了給學生印試卷中有利可圖,便琢磨如何利用手中的權力中飽私囊。爲保密需要,鍾某等人把全市中小學的單元試卷都放到廣昌縣某印刷廠印。鍾某與教研室的另兩名副主任,便與印刷廠共同玩起了"貓膩":採取提高單價虛開發票的手段套取差價款。他們背著教研室的其他職工,將原本2分9釐一張的試卷,籤合同時提高至3分4釐。幾年間,三人各分得近4萬元。檢察機關認定鍾某等三人私分此筆錢是涉嫌受賄犯罪。
在籤合同時提高了一次價錢後,鍾某等人在結賬開發票時,又一次將試卷價格提高到每張4分3釐-4分8釐不等,這次得到的差價則作爲教研室的"獎金","發"給每一個工作人員。該教研室前後共有11名工作人員被捲進此案,每人分得2萬餘元。檢察機關認定這是該教研室涉嫌集體貪污。在私分過程中,鍾某等三名正副主任與出納、會計5人清楚這些錢的"來歷",另外6人則不清楚真實的情況,檢察機關認定這6人不構成犯罪。
自1996年以來,瑞金市的中、小學及在校生逐年遞增,現已有中小學270多所,在校學生8萬多人。據檢察機關查證,四年中,瑞金市教委教研室共從280多萬張試卷中套出印購試卷費50餘萬元,除了10餘萬元被用於送禮等不正當開支外,其餘均被私吞瓜分。
目前,瑞金市教委教研室的主任鍾某及兩名副主任和出納、會計等5人,已被瑞金市檢察機關的偵查部門移送審查起訴部門審查起訴。(周文英、溫斌、朱小平)
同時看完上面的這三條消息,你會有什麼樣的感想?難道你不感到憤怒嗎,難道你不覺得有什麼東西堵在你的心口嗎,難道你還能無動於衷地麻木下去嗎?這樣的東西如果是單獨地出現在我的面前,也許我還不會感受到如此令我幾乎要窒息的激憤,因爲,畢竟窮人一直以來就這麼窮著,窮掉了活著的樂趣窮掉了自己應得的權利,但是,爲什麼要讓我看到這樣的對比呢?這用來維繫席飛半個月生活的10元錢,給席飛的那兩個被選爲「賊」的同學帶去的卻是靈魂的創傷,給席飛的老師帶去的是抹不去的愧疚。可是,這10元錢,對那些貪官污吏來說,能算得上九牛一毛麼?!在這兩種生態的人面前,你的感受用什麼語言能夠表達?
我有一箇中學同學,讀大學的時候我們兩人的學校相隔很近,她是學醫的,我學的是機械製造,我們兩所學校的中間隔著的是黑龍江大學。大學畢業後一開始我們還聯繫了幾年,後來,她突然間就失蹤了。在失去聯繫將近十年的時候,她突然打通了我的電話,接電話的時候我一時都懵了,把她當成了另一箇中學同學。她來看我,我們幾乎聊了幾個通宵,說的無非是那些二十多年前的往事。她說她到大學裏第一頓飯吃饅頭的時候淚流滿面,因爲她想起了還在農村黑土地上求生存的父母仍然在家裏就著大蔥吃那又硬又粗的苞米麵餅子,她說她小的時候看母親給生病的奶奶做了一次雞肉水餃,當時饞得不行,就想,自己什麼時候能當上婆婆也這麼享受一回?她說的時候我們兩個都哭了。那就是我們的童年生活,我們上大學那年是1980年,那時候,生活在農村的老百姓的日子和現在的席飛的爺爺相比有了多麼大的改變了嗎?也許,那時候的貧窮老百姓和現在的貧窮老百姓之間的惟一差別就是數量上有了點不同,那時候像我的同學的父母那樣的農民到處都是,現在像席飛這樣的情況是屬於少數。可是,二十年過去了,二十年的時間裏我們依然沒有消除貧窮,但是,二十年間我們的貪官污吏貪污受賄的「水平」可是提高了多少倍啊。
新中國成立了五十多年了,可是,五十年間我們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有了多大的提高?五十年過去了,還有多少生活在貧困農村的老百姓活著惟一盼望的就是「能過上不愁吃不愁穿的好日子」啊。想起這些就不能不讓人心酸落淚,現在,又有大批的城市下崗人員的孩子加入到了「讀不起書」的行列,面對老百姓這樣的生存狀態,我們還有什麼臉面在那裏做盛世歡歌狀?盛世,誰的盛世?
誰對得起中國?
讀張愛玲寫於1943年的文章,在時間的距離上,這些文字距離現在已經是快六十年了,但我仍然沒有感覺到時間的流逝。張愛玲不同於魯迅,她是從來不想讓自己的文字去涉及什麼時事的,但是,於不經意間她筆下的文字還是讓我感到驚奇,她在《洋人看京戲及其他》裏面這樣寫到:
「多數的年輕人愛中國而不知道他們所愛的究竟是一些什麼東西。無條件的愛是可欽佩的──惟一的危險就是:遲早理想要撞著了現實,每每使他們倒抽了一口涼氣,把心漸漸冷了。我們不幸生活於中國人之間,比不得華僑,可以一輩子安全地隔著適當的距離崇拜著神聖的祖國。」
是啊,多數的年輕人都是愛國的,而在很多的年代,年輕人之愛國到最後竟然會愛出罪來!我們愛中國卻不知道自己所愛的究竟是一些什麼東西嗎?
就像我在幾年前對別人說我要寫《誰對得起中國?》的時候,別人也問:什麼叫「對得起」中國?你要「對得起」中國的什麼?誰需要你對得起中國?我爲什麼要對得起中國?中國對得起我麼?
幾年來我自己也一直在不停地問自己這些問題,問得我自己頭都大了多少次,心也冷了多少次!頭大心冷,是因爲我想起了譚嗣同、秋瑾、李大釗,想起了劉和珍,想起了遇羅克、林昭、張志新,還有那個手拿「人血饅頭」的華老栓以及他的用了人血饅頭卻仍然沒有治好病的兒子。
讓我們看看魯迅寫於1925年4月29日的《燈下漫筆》──
「但我當一包現銀塞在懷中,沉墊墊地覺得安心,喜歡的時候,卻突然起了另一思想,就是:我們極容易變成奴隸,而且變了之後,還萬分喜歡。」、「假如有一種暴力,『將人不當人』,不但不當人,還不及牛馬,不算什麼東西;待到人們羨慕牛馬,發生『亂離人,不及太平犬』的嘆息的時候,然後給與他略等於牛馬的價格,有如元朝定律,打死別人的奴隸,賠一頭牛,則人們便要心悅誠服,恭頌太平的盛世。爲什麼呢?因爲他雖不算人,究竟已等於牛馬了。」、「但實際上,中國人向來就沒有爭到過『人』的價格,至多不過是奴隸,到現在還如此,然而下於奴隸的時候,卻是數見不鮮的。」、「任憑你愛排場的學者們怎樣鋪張,修史時候設些什麼『漢族發祥時代』、『漢族發達時代』、『漢族中興時代』的好題目,好意誠然是可感的,但措辭太繞彎子了。有更其直截了當的說法在這裏──一、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二、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這一種循環,也就是『先儒』之所謂『一治一亂』;那些作亂人物,從日後的『臣民』看來,是給『主子』清道闢路的……」
從時間上看,1925年的那個時代跟我們現在的生活是沒有可比性的,那時候距離法西斯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還有一段距離呢,而現在的我們不是已經早就遠離了法西斯時代了麼?可是,當我讀魯迅的這篇文章的時候,卻從來都沒有感覺過時間的流逝。
誰對得起中國?
也許,發出這樣的一句問話,我在一些人的眼裏立即就會成爲另類,但是,我覺得我有權利和責任問這麼一問,我的這個感覺還是從我兒子那裏得到的。記得在他剛剛五歲的時候,我命令他去做一件事情,他不願意去做,於是,他就站在牆邊歪著頭很不服氣地問我:「小孩也是人,爲什麼小孩就總得聽大人的呢?」是呀,我們已經聽了太多太多的「大人」的話,我們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大人叫幹啥就幹啥」的「好孩子」,我們很少用自己的頭腦去想一想自己爲什麼要聽「大人」的話,我們更是很少去想想「大人」的話到底在多大程度上的對的。中國人的做「好孩子」的思想,其實在某種程度上是被逼的,在趙高專權的時代,誰敢說鹿不是馬?
在經歷過太多次的指鹿爲馬以後,大多數聰明的中國人都學會了拍馬,以至於在今天,拍馬已成了一種氣候、一種生存方式、一種大家都幾乎認爲是非常正當的手段。但是,因爲性格的因素,我還是學不會拍馬,而且,我也不能允許自己也混跡於那樣的一羣拍馬者的行列。我知道,拍馬,在表面上看是「拍者」和「馬者」自己的事情,但是,稍一動腦,我們就能知道,許多對大多數人嚴重不利的事情,就是那「拍者」和「馬者」在背後達成的交易,所以,我對拍馬感到十分的厭惡,厭惡那副沒原則地喊「好好好」、沒是非地說「是是是」的嘴臉。而且,一個人、一個社會,如果過分地喜歡別人拍馬,喜歡好大喜功,喜歡報喜不報憂,就離危險的邊緣不遠了。
所以,我要發出這樣的另類的聲音,大聲地問:誰對得起中國?
(中國事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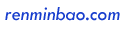





















 打印機版
打印機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