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高行健,先向你道賀。也有不少朋友託我轉達他們的祝賀。你的好友劉心武人在南京,我還未聯絡上,他妻子託我轉達他們全家的問候和祝賀。
高:非常感謝,不管是老朋友還是新朋友,他們的情誼都令我十分感動。
孔:剛獲知你得獎,便給你打電話,一時間怎麼也打不通,只好先發傳真,請你回電話。
高:這邊的巴黎電信局一知道我得獎的消息,就主動將我的電話號碼從可以讓公衆查找的電腦裏消除,變成一個保密的電話號碼。這雖然給我減緩了不少壓力,卻給大家帶來不便,真是抱歉。
孔:我知道你在1993年就已獲得法國文化部頒發的藝術與文學的騎士勳章,當時是表彰你的戲劇與現代水墨畫的創作成就,這次則因爲你的戲劇與小說創作成就而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是這樣嗎?
高:是。
孔:你在國內創作並上演的《車站》、《絕對信號》、《野人》,在中國戲劇界和文學界都有頗大影響,甚至可以說你是中國「現代主義戲劇之父」,我只是在陳述一種事實,雖然先鋒戲劇在西方早就有了,但在你這幾部戲之前,中國並無此類戲劇,這是載入戲劇史的。
高:我還記得當年《車站》與《絕對信號》在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實驗小劇場「內部觀摩」演出的情景,當時你也來了。
孔:是的,我也記得,看完戲就到小劇場後面你的「陋室」喝酒。記得《野人》我看的也是首演,完了又到你那裏,你的先鋒戲劇已經由小戲變成大戲,可你還住在那間六、七平方米的斗室裏。
高:我在巴黎住的也是普通的公寓。
孔:很遺憾,你到了法國之後創作的新戲,我一場都沒看過。你總共創作了多少部戲劇?
高:算上國內已搬上舞臺的三部戲和未能上演的《彼岸》,大約是十八部吧,象《逃亡》、《生死界》、《對話與反詰》、《夜遊神》、《週末四重奏》、《山海經傳》和寫六祖惠能和中國禪宗的《八月雪》,最近完成的是《叩問死亡》和另一部還放在抽屜裏的《天使的日記》。
孔:我知道你的《對話與反詰》也是取材禪宗公案的。你能說說其它幾部劇作嗎?
高:譬如三幕劇《逃亡》,這部戲曾在中國國內被作爲「反革命教材」內部印刷供批判用,還配上了我的漫畫頭像,這個「特殊文本」還是你給我寄來的,你有空記得再給我複印一份,這是難得的紀念。《逃亡》這部戲最先由瑞典皇家劇院首演,後又在德國、英國、法國等多個國家上演。譬如在波蘭演出,波蘭人認爲,這演的就是我們經歷過的時代,他們將這部戲完全按現實主義的手法來導演;這部戲在法國演出時,評論界指出「這就是今天正發生在巴爾幹科索沃的事情,高在好幾年前就寫出來了」。《逃亡》還在日本由兩個不同的劇團改編上演。有趣的是,這部戲還在非洲演出,那個劇團好象在多哥。他們將劇本改編成非洲式的戲劇,即是用街頭遊行的狂歡式演出。這個非洲劇團馬上就要來法國利爾市,演出非洲式的《逃亡》。
孔:我看過《逃亡》和《生死界》的中文劇本。
高:《生死界》最早在巴黎圓環劇院首演,後來也在歐洲很多國家上演。三年前也到過美國演出,也就是我到你新澤西的家過春節那次,我是去協助導演那部戲的。
孔:我知道你以前在中國寫的戲劇也一直在國外上演。
高:對,歐洲亞洲都在演。臺灣、香港都演出過《車站》,日本最近還演過。日本戲劇界的朋友專門來巴黎找我,他說這部戲就是爲我們日本寫的。你想想,《車站》當時在國內被認爲是諷喻中國現實的荒誕劇,而日本與中國的現實相距多遠!還有,《車站》在奧地利演出,劇場是維也納皇宮廣場旁邊一個新落成的地鐵站,在啓用之前一個月,《車站》在那裏上演。他們將原來劇中的「小痞子」處理成一個頹廢的青年「朋克」的形象;又將原來劇中的「馬主任」變成一個女角,操一口老套僵死德語,活脫脫一個女官僚!首演時我也去了,觀衆從頭笑到尾……你看,這說明了這部戲的世界性。
孔:你的劇作都寫中文法文兩個文本,對嗎?
高:大部分都是,我的劇本通常是歐洲的一些劇院、戲劇基金會訂購的。手頭這部《叩問死亡》中文劇本還未動筆呢,因爲這戲是法國文化部訂購的,當然先寫法文的本子。
孔:但你的小說都是用中文寫,不是嗎?
高:那當然,我用中文比用法文得心應手一百倍!不過用另一種語言寫作,對我來說也是很有趣和很刺激的,所以我今後也不會放棄法文寫作,但我始終是一個使用漢語的中文作家,這是毫無疑問的。
孔:你的長篇小說《靈山》,除了法文瑞典文翻譯本之外,英文本也出來嗎?
高:英文譯本五個月前在悉尼出版。翻譯者是悉尼大學中文系教授梅勃爾,他的譯文非常漂亮。《靈山》英文版已賣斷給澳州最大的一家出版社,我得了這個諾貝爾文學獎,美國幾家出版社爭著要出《靈山》,但版權已不在我手裏,怎麼處理是他們的事了。
孔:你獲獎之後,國內作家的最初反應你知道嗎?
高:我還不知道。
孔:我大略跟你說說吧。我所知道的活躍在第一線的幾位中年作家表態均不錯,他們的主流意見都認爲高行健是個出色的作家,都爲你獲獎而高興,進而他們也認爲國內也有不少好作家,這些人也有可能、有資格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這種意見當然是完全成立的。
高:對。
孔:作家當中有些人泛出「酸葡萄心態」,也是難免的,但最失水準的就是中國現代文學館館長、老舍的兒子舒乙,他說這是「開了中國人一個大玩笑」,他把諾貝爾文學獎當作是全體中國人的大事,又說1968年諾貝爾文學獎本應是授給他父親老舍的,只不過瑞典漢學家馬悅然到了中國,得知老舍已自殺,這才授予日本的川端康成。
高:他真是這樣說的?
孔:我在網上看到的。他好象認爲馬悅然一個人掌握著諾貝爾文學獎的決定權。我們都認識馬悅然,也都多少知道老舍沒能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原因,那是中國激盪的政治生活所造成的悲劇,不過那絕對早於1968年,這事在1957年就註定了。其中細節當然要留給馬悅然自己願意說的時候才說,我們不能代他立言。
高:況且1968年馬悅然也沒去過中國,那時誰能去中國?
孔:當然老舍是中國二十世紀傑出的作家。
高:對,老舍是非常優秀的作家。
孔:不過舒乙看來就沒有乃父之風了,他的立場和中國作家協會發言人的說詞是大致相近的。
高:我也不知道中國作協說了什麼。
孔:代表中國作協表態的那個人,你和我都認識他,就是金堅範。他是從對外友好協會調到中國作協對外聯絡部任領導的,算是當過你的頂頭上司吧。他說:「高行健當年在作協外聯部工作時,我們所有人都認爲他的作品非常平淡。」他又說「高行健是個法國作家,不是中國作家。他的得獎和中國毫無關係,也沒什麼可值得高興的。」
高:他這樣說我一點也不覺得奇怪。
孔:問題是他代表中國作家協會出來發言,金堅範現在是中國作協的一個什麼書記,他從來就不是作家,除了寫總結報告,從來沒寫過一行和文學作品有關的字句。他有什麼資格代表作家表態?誰賦予他這種權力?他的說詞對中國作家和中國文學都是一種侮辱。所以我要告訴你另一羣青年作家的態度,你不會認識他們,他們也不會認識你,但這幾位都是現時文壇上相當活躍的作家。他們聯名強烈抗議中國作家協會的立場態度,認爲嚴重傷害了作家的名譽和中國文化的尊嚴,要求中國作協公開道歉。
高:這世界上總有不受思想專制所控制的人。
孔:問題在於金堅範的言論不是他個人即興的表態,青年作家的抗議恐怕只成了「鐵屋裏的吶喊」,這和奧運「王麗萍金牌風波」引來的公衆抗議不一樣,那一回合倒是民衆嬴了。我剛剛得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朱邦造這樣說:「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最近的行動表明,諾貝爾文學獎已經被用於別有用心的政治目的,不值一評。」顯見得,這是整個官方設定的立場。
高:這並不令我意外。當年我的戲劇在國內受盡批判,那比荒誕戲劇還要荒誕。而且荒誕戲劇是通過思辯去發掘生活與時代的荒誕性,而在中國,現實就是那麼荒謬。我想這些都不用去理會它。
孔:你在中國生活了四十七年,你憑自己的戲劇、小說,還有文學理論,已經在中國文壇立身揚名,你至今用母語寫作,並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只有極權專制到不可理喻的政府才會任意剝奪你「中國作家」的資格。按這去推論,楊振寧、李政道也是外籍華人,他們獲獎也應該「和中國毫無關係」,「不值一評」和「沒什麼可值得高興的」?
高:這就是我說的比荒誕劇還荒誕。
孔:諷刺的是,被認爲有臺獨傾向的陳水扁倒向你道賀。他說這對以中文創作的作家及讀者「是一件非常令人振奮的事情」,他「代表臺灣政府和人民向高行健先生表示恭喜之意,也爲其卓越成就表達最高的敬意。」臺灣立委還建議將瑞典皇家文學院的頌詞列入國會記錄。同樣是中國人和中國文化,兩岸真有天淵之別!當然,文學是個人的事情,也是無國界的,作家不會把自己的作品和成就當作國家和民族的榮耀。但任何一個健康正常的政府,都會尊重自己的作家藝術家,那也是身爲政治家起碼的文化情懷,他們應該樂於把個人創造的藝術成就看作自己國家和民族所貢獻出來的優秀文化,雖然有時作家不願意領這份情,比如日本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大江健三郎,但日本政府也絕不會因此對他惡言相向。而你呢,我沒有聽到江澤民說什麼,倒先聽到陳水扁來代表「政府和人民」,還代表「以中文創作的作家和讀者」來道賀。
高:我還不知道陳水扁的賀詞,倒是法國總統希拉剋和總理若賽爾馬上發來了賀電和祝詞,他們認爲這是法國的光榮。
孔:1993年你獲得法國政府的文學與藝術騎士勳章,你還是中國籍的作家,他們一樣認爲你的成就是法國和法國文化的光榮,這是一個文化大國的胸襟。而在中國,政府官方首先剝奪了你的資格,再貶低你的成就,更禁止中國的人民分享你的這份光榮。
高:我在中國大陸生活了這麼久,已經熟悉了那種思維方法,這是一種習慣性的延續。所以,我到了海外和國內作家朋友聯繫很少,幾乎沒有直接的聯繫,因爲我不想給他們帶來任何麻煩,當然對老朋友還是很惦記的。
孔:高行健,我們不妨來作一個假設。你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在某種角度來說,和當年其他華人獲得諾貝爾獎的價值是等同的。你認爲大陸官方在經過最初的尷尬和強烈的牴觸之後,會不會漸漸覺出,這其實也不是一件壞事,於是允許國內劇壇重演你當年的幾部戲呢?
高:哦,這不可能。官方現在發表的言論和設定的立場,以他們過去對我的態度來參照,倒是十分符合他們的邏輯。相反,批准上演我的戲劇,是完全不可能的。我們可以讓時間來驗證。
孔:江澤民說「我欲乘風歸去」,兩年之後,北京政壇人事一新,而你獲諾貝爾文學獎的連鎖效應,在兩年後也漸漸沉澱下來了。大陸當權者的感受或許也有所變化。楊振寧、李政道等一直是北京的席上貴賓,也許僅出於統戰需要,他們也會對你網開一面?
高:文學與物理和其它學科畢竟不一樣。文學不是政治,卻也和意識形態有關。他們可以歡迎一個科學家,但我想,在我的有生之年都會在他們的名單之外,或者說是在他們的另一個名單之內。我也無所謂了。
孔:有生之年?你太悲觀了!我們還是來談文學吧,我好象記得在八十年代,「自我放逐」這話是你最先在國內說的,比後來的「流亡文學」早得多。
高:流亡就是精神上的自我放逐。中國不是一個國家概念,對我來說,中國朋友就是中國,中國文化就是中國,臺灣香港也是中國,甚至新加坡馬來西亞也有濃郁的中國文化,還有美國的紐約、舊金山……我覺得,一種華人基因的文化,正在生長和傳揚,這就象英語世界一樣,我想,除掉那些倒賣辮子和小腳的「假古董」的二道販子,真正的華語文學、華人文化正在產生越來越強大的影響。想想人家猶太人,他們的文化生存要比華人困難得多,人家不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孔:所謂自我放逐不是逃遁,而是一種反抗,一種再生,一種創造,所以到處都是我們的精神家園。
高:我的得獎只是一個開頭。因爲並不是所有作家藝術家都生活在專制極權制度之下,就算國內也總有不受到控制的人,而且好的作家越來越多。我覺得,一個繼承中國文化傳統並且能與其它文化溝通的「泛華語文化」,在新世紀裏的生命力將更加強大。她在世界舞臺的崛起,是指日可待和正在發生的事情。轉自(民主中國)
(http://renminbao.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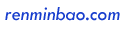












 打印機版
打印機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