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物主上帝是多么奇妙啊!漫步其间,每一个角度都是英国水彩画。“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大自然周而复始地新生,反衬出人的尴尬来:在这生机勃发的天地间,人却年年老去;油画般的美景中,人永远都是匆匆过客。一百多年前,流放西伯利亚的十二月党人,还能与俄罗斯的森林相映衬成趣,而我这个政治流亡者,在这里永远是个尴尬的多余人。
清明时节,忽生祭吊亡父之心。2008年去国后,不上坟已四年,不知亡父坟头,是否蒿草没人?
先父年轻时,就像王希哲先生一样,狂热崇拜毛太阳,文革时一跃而跻身桂林革命工人造反司令部“首长”行列,旋即因反对武斗而身陷囹圄,“联子”进城后又因“造反派”经历,再蹲大牢,几乎被枪毙...八十年代“平反”后,转而崇拜邓小平,口口声声“邓伯伯”...及至“六四”枪响传来,终于绝望病死。可惜先父至死抱着马克思不放,总以宗教为精神鸦片,无神论一条路走到黑,祈求上帝免他的债罢。先父的悲剧启迪世人:人有崇拜的本能,若不皈依正教,就必为马克思、毛泽东、邓小平等妖魔所迷惑。
先父教育理念也错谬多多,既忽视幼教,又不尊重人的兴趣,自以为只要受得锥刺股,人皆可成科学家,孰不知这种石头能孵鸡的理念,与“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有什么区别?
但先父也有他的优点:好学不倦,思维敏锐、艺术鉴赏层次不俗、二胡、小提琴皆无师自通、钢笔、毛笔书法也达准专业水平,这些,于我,于家人,不可能没有影响。
先父中等身材、长头秃发、气宇轩昂,长相酷似蒋介石,单位邻里闻名,加之善于辞令、滔滔不绝,可谓饰演蒋中正的天生特型材料,也是当律师的好料子,亲朋好友中颇有劝他考律师的。可惜,随着英年早逝,一切天分都深埋入土了。斯已入土,呜呼哀哉!
清明,正值桂林桃花盛开、映山红摇曳的时节,俗话说“雾重庆雨桂林”,往年的清明,老家桂林几 乎总是阴雨连绵、泥泞不堪,上坟路上,车塞车,人挤人,本来有诗曰:
“清明时节雨纷纷,
路上行人欲断肠;
借问酒家何处有?
牧童遥指杏花村。”
唐宋时期的清明节有这种意境,不等于现在还有。看看上坟路上众人脸上的烦躁、庸俗的表情就知道:一切不过是走过场。上坟的坟头上,震耳欲聋的鞭炮声到处炸响,乌烟瘴气,男女老幼呛得鼻涕眼泪横流,恨不能赶快烧掉“纸钱”、“冥币”,离开这难挨之地。哪有什么寄托哀思、吊祭亡灵的空间和意境?
我羡慕欧洲人祭吊死者的安静,没有安静,岂有内省?从上坟的“习俗”,可以看出现在的中国人缺乏内省;而喜好安静,实在是德国人音乐、哲学、科技皆高度发展的重要原因。
唐、宋时期很少放鞭炮,所以唐人、宋人清明节上坟,可以一边烧着纸钱,一边安安静静地遐思默想,那时的中国,与现在的中国,一定是两种境界。鉴赏唐诗宋词,总不免钦佩日本人的鉴别力,日本人完美地保留了隋唐服饰建筑工艺、宋代花灯纸谜,可就是不学中国的小脚、太监、鞭炮,对猪尾巴的满清,更是不屑一顾。我中华之精华,在日本而非在中、港、台也。
他年若有幸归国上坟,我决不在清明节去,而选择一个安静的下午,望褂子山下的坟头,插上一束白雏菊,然后静静地待上一时半晌。我知道,生前爱花的父亲,早已不在坟里,他在风中,在林间,在新绿的野原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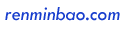


























































 打印机版
打印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