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物主上帝是多麼奇妙啊!漫步其間,每一個角度都是英國水彩畫。「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大自然週而復始地新生,反襯出人的尷尬來:在這生機勃發的天地間,人卻年年老去;油畫般的美景中,人永遠都是匆匆過客。一百多年前,流放西伯利亞的十二月黨人,還能與俄羅斯的森林相映襯成趣,而我這個政治流亡者,在這裏永遠是個尷尬的多餘人。
清明時節,忽生祭弔亡父之心。2008年去國後,不上墳已四年,不知亡父墳頭,是否蒿草沒人?
先父年輕時,就像王希哲先生一樣,狂熱崇拜毛太陽,文革時一躍而躋身桂林革命工人造反司令部「首長」行列,旋即因反對武鬥而身陷囹圄,「聯子」進城後又因「造反派」經歷,再蹲大牢,幾乎被槍斃...八十年代「平反」後,轉而崇拜鄧小平,口口聲聲「鄧伯伯」...及至「六四」槍響傳來,終於絕望病死。可惜先父至死抱着馬克思不放,總以宗教爲精神鴉片,無神論一條路走到黑,祈求上帝免他的債罷。先父的悲劇啓迪世人:人有崇拜的本能,若不皈依正教,就必爲馬克思、毛澤東、鄧小平等妖魔所迷惑。
先父教育理念也錯謬多多,既忽視幼教,又不尊重人的興趣,自以爲只要受得錐刺股,人皆可成科學家,孰不知這種石頭能孵雞的理念,與「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有什麼區別?
但先父也有他的優點:好學不倦,思維敏銳、藝術鑑賞層次不俗、二胡、小提琴皆無師自通、鋼筆、毛筆書法也達準專業水平,這些,於我,於家人,不可能沒有影響。
先父中等身材、長頭禿髮、氣宇軒昂,長相酷似蔣介石,單位鄰里聞名,加之善於辭令、滔滔不絕,可謂飾演蔣中正的天生特型材料,也是當律師的好料子,親朋好友中頗有勸他考律師的。可惜,隨着英年早逝,一切天分都深埋入土了。斯已入土,嗚呼哀哉!
清明,正值桂林桃花盛開、映山紅搖曳的時節,俗話說「霧重慶雨桂林」,往年的清明,老家桂林幾 乎總是陰雨連綿、泥濘不堪,上墳路上,車塞車,人擠人,本來有詩曰:
「清明時節雨紛紛,
路上行人慾斷腸;
借問酒家何處有?
牧童遙指杏花村。」
唐宋時期的清明節有這種意境,不等於現在還有。看看上墳路上衆人臉上的煩躁、庸俗的表情就知道:一切不過是走過場。上墳的墳頭上,震耳欲聾的鞭炮聲到處炸響,烏煙瘴氣,男女老幼嗆得鼻涕眼淚橫流,恨不能趕快燒掉「紙錢」、「冥幣」,離開這難捱之地。哪有什麼寄託哀思、弔祭亡靈的空間和意境?
我羨慕歐洲人祭弔死者的安靜,沒有安靜,豈有內省?從上墳的「習俗」,可以看出現在的中國人缺乏內省;而喜好安靜,實在是德國人音樂、哲學、科技皆高度發展的重要原因。
唐、宋時期很少放鞭炮,所以唐人、宋人清明節上墳,可以一邊燒着紙錢,一邊安安靜靜地遐思默想,那時的中國,與現在的中國,一定是兩種境界。鑑賞唐詩宋詞,總不免欽佩日本人的鑑別力,日本人完美地保留了隋唐服飾建築工藝、宋代花燈紙謎,可就是不學中國的小腳、太監、鞭炮,對豬尾巴的滿清,更是不屑一顧。我中華之精華,在日本而非在中、港、臺也。
他年若有幸歸國上墳,我決不在清明節去,而選擇一個安靜的下午,望褂子山下的墳頭,插上一束白雛菊,然後靜靜地待上一時半晌。我知道,生前愛花的父親,早已不在墳裏,他在風中,在林間,在新綠的野原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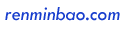


























































 打印機版
打印機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