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澤農爲臺灣讀者簽名 |
|---|
淋浴後,趁喬爾在收拾行李,我把自制的這面橫幅塞入褲腰,然後抽出,就這樣反覆練習著。按計劃,我們屆時會高舉起一面大型橫幅,多數人坐在橫幅前打坐,十分鐘後離開。我的橫幅是備用的,以防原定那面大橫幅不能帶進廣場。萬一計劃進行得不順利,警察很有可能包圍我們,那麼能否動作迅速地展開橫幅就至關重要了。我試了幾遍之後,覺得那已是我的最快速度。此時喬爾已把我的行李收拾妥當,準備幫我帶到機場。我已無任何後顧之憂,是去廣場的時候了。
我們已經預訂了返程機票,班機將在發起行動的四小時後起飛。我準備完成使命後就近叫一輛計程車,直奔機場;但若在迫不得己的情況下,就乾脆朝機場的方向撒腿飛奔。儘管天安門廣場警察的兇惡已經臭名遠播,但我們知道也曾有很多人能夠憑藉智慧毫髮未傷地離開了廣場。
大約早晨八點,又到了再次分手的時候。我又一次眨眨眼,笑著與他握手道別。這回,喬爾說:「機場見!」
……
十五分鐘後,我已經漫步在天安門廣場邊的人行道上。我渾然不覺自己剛剛走過了天安門廣場派出所的正門。廣場上到處是警察,但我肯定當我們在廣場上聚集時,警察已經散去。廣場對面,一隊身穿黑色制服的中共官員正步入人民大會堂。我估計是上班時間到了,同時自娛地想:「也許他們下午兩點會到廣場上□達□達?」
我步入街對面的一個公園,漫無目的地逛了一會兒,然後從邊門走近紫禁城,發現自己正好面對故宮博物院的正門。儘管很想進去參觀一下,但又不想分心,此時的我極其需要保持平靜,因爲內心的一種緊張情緒,正在竭盡全力衝上我的頭腦,試圖讓我恐懼,讓我恐懼得不能自持。我轉身走了出來。
時候尚早,但人們已經開始湧進來,我感到自己像一葉輕舟漂浮在人羣的海洋上。他們都快樂地沈浸在他們的古文化遺蹟中。如果他們知道的話,這不過是轉瞬即逝的快樂。
我,一名二十三歲的年輕人,正在走過紫禁城。就在昨天晚上,我被告知,我所說的話是「禁言」。事實上,我準備要做的事情,也是中國那個獨裁者嚴令禁止的。它用它那敗壞了的權力和觀念扭曲著對與錯。它強迫警察、軍隊、政府、學校、醫院、勞教所、工廠和社會各階層抓捕法輪大法學員,用它的話說,要「消滅法輪功」。法輪功學員經受了最可怕的酷刑折磨,有些人並因此而死去。他們的國人被告知法輪功學員正受到「人道主義」對待;國際社會被告知現在是中國「人權最好的時期」。當善良的中國人被告知其他國家也禁止法輪大法時,他們把身旁修煉大法的家人和親朋好友交給「當局」處理,並確信自己這樣做是對的;當中國被授予奧林匹克運動會主辦權時,中國主席以此爲藉口聲稱對法輪功的鎮壓是對的,還要加強鎮壓。無論那個獨裁者通過了多少政策或者編造了多少謊言,在歷史、人類和上天的眼中,它、它的幫兇,以及它的迫害才真正是應該被禁止的。
我走向紫禁城的正門,穿過遊客的人流,所有的噪音都變成了低微的細語。我不禁思緒如潮:他們的中國文化是由偉大的領袖、勇士、文人和其他傑出人物構成;他們所擁有的一切不朽的作品、遺蹟都來自那些以美德和智慧創造中國文化的人們。這些中國人在富麗堂皇的紫禁城裏漫遊,試圖捕捉住他們輝煌文化的一個片段。如果他們知道現實生活中在發生著什麼,他們的笑容就會消失,真相會震撼他們的心靈。這些旅遊者們希望一睹爲快的所有光彩奪目的東西,實際上都已不復存在。皇冠上的黃金現已被油漆代替,原來的金子已被竊賊盜走。
如今的情況又怎樣呢?當我們把今天當政的國家主席與唐太宗這樣一位被中國人譽爲最偉大的皇帝相比,就會發現,今天的主席就像一種病害,侵蝕著中國社會的肌體。可是,即使是唐代,這個被廣泛譽爲中國五千年曆史中最昌盛的朝代,也會有終結的一日。我們人類經歷生、老、病、死的過程,中國各朝代也不能逃脫成、住、壞、滅的必然法則;在整個人類歷史過程中,其他文明國家也無不如此。對此,我顯得那麼渺小而無力,我能做得了什麼呢?這種認識幾乎令我拂袖而去,掉頭直奔機場了。然而,我來,不正是爲了告訴這些中國人真相?!那種感覺不應該阻止我做正確的事情。作爲人,我們不是總能夠去選擇我們在生活中將要發生的一切,但是如何去面對它,卻是可以選擇的。我的選擇很明確,那就是繼續按計劃進行。
我經過紫禁城巨大的鐵門,天安門廣場盡收眼底。當我行過金水橋時,一名警察進入了我的視線。我悚然看到他的手裏拎著一根電棍,用來輸送電流電擊受害者的那一端暴露無遺。雖然多數武器都配有皮套,他則是把電棍緊緊地抓在手上。我的目光順著他的身體移向他的雙目,只見他下巴向下挪了一下,眯起眼睛,用兇巴巴的眼神打量著我。很多警察都有這種暴躁的表情,但是這個警察尤甚,看上去特別嚇人。我得說,他的這種表情真的起了作用。
走過他的身邊時,我的腦海裏閃現出各種殘暴折磨的景象:我被綁起,赤裸著倒在地上,全身各處遭到重踩和毒打,無數電棍電擊著我,令我疼痛難忍,發出一聲聲痛苦的慘叫,隨即一根電棍捅進我的嘴裏,我的聲音立刻被悶住。就在這顫抖的身體、翻著眼白的景象在我的腦海裏打轉時,恐怖感再次壓了下來。發生在許多中國法輪功學員身上的這種可怕而極度痛苦的處境很快會發生在我的身上嗎?我止步,搖搖頭,拍拍腦門兒,堅定地對自己說:「振作!」總是這樣神經質沒有任何好處,我清理了一下自己的思想,走進了紫禁城旁邊的公園。
那天早晨天氣很涼,我找了一個可以曬太陽的長凳坐下來看書。每一次我的目光離開書本,掃視前方時,我都有一種強烈的慾望,要起身和我周圍的人們傾談。想到這些人在他們自己的國家裏受矇蔽,我的內心裏產生了一種揮之不去的空虛感。我不停地對自己說:「忍耐!忍耐!」我繼續看書,保持冷靜。
又讀了一會兒,感覺餓了,於是在公園裏找了一個地方吃東西。我不斷地看表,每看一次,胃都會因焦慮和恐懼而緊縮起來。由於在公共場合不能採用打坐姿勢,我就按照平時發正念的要求,開始清理自己:意識清楚地、堅定地在意念中剷除不好的思想念頭、業力、不好的觀念和外來干擾。我越能夠保持平靜和堅定,就越能夠鬆弛我的緊張情緒。在銷燬所有不好的思想和觀念的同時,真善忍的美好就不再是紙上的字和頭腦中的理解,也不僅只是我心中的純淨感覺;她不僅是我所體驗和熱望實踐的法理,而且已經成爲我的一部分,應該說,我已經成爲她的一部分。這種與生活、與宇宙中萬事萬物的不可分離性從我生命的深層升起,無以言表。在這一天中,我多次看表,每一次我都有同樣的感覺,唯一不同的是,我的緊張情緒越來越弱,越來越少;而我心中之光越來越強,越來越明亮,就好像多年來一直存在於我身上的許多不好的觀念──憤怒、英雄主義、名聲、妒嫉心、貪慾、恐懼心等等,所有你視爲毒藥的東西都一起跳了出來,企圖毒害我的大腦,但是每一次,它們都毫無例外地在真善忍的慈悲力量中被銷燬。儘管我大部分時間都是坐在公園的一張長凳上,而在我的內心中卻進行著一場善與惡的激烈交鋒。爲了在即將開始的行動中走好每一步,我一定要保持清醒、慈悲和正念。就這樣,在離開公園之前,這種淨化思想的過程一直在不斷進行著。
已經是差一刻兩點了,還有約十分鐘的時間。我充分利用這十分鐘的每一分、每一秒來積極純淨自己的思想、心靈和一切可能有的不好的因素,不允許壞思想出現。儘管這種內心活動過程很難用語言來表達,我願意儘量描述一下我在公園的最後幾分鐘裏的思想狀態──
這就好像我全身所有的細胞粒子,溫暖而具活力地震顫著。隨著清理我生命的每個部分,我進入了自己生命中的又一微觀層次,感覺就像慈悲力量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迸發、擴展。我可以感到自己整個生命的粒子都在發生變化。善愈向微觀擴展,生命就愈加浩瀚。我的精神和思想成爲了一體,像宇宙一樣洪大無邊。儘管表面上我只是一個走在中國公園裏的年輕人,但是在內心中,我感到自己每走一步都震動著十方世界,我甚至有意地放輕了自己的步伐。我身體最表面的一層情感永遠都不會體會到這一經歷,只是暫時處於睡眠狀態,而身體更深層、更宏大的部分,則深深地被真善忍的偉大力量所感動。
在鎮壓法輪功初期,那個獨裁者認爲它可以輕而易舉地剷除法輪大法,因爲法輪大法學員修煉真善忍,它認爲修煉真善忍會使人軟弱無力。然而,正是因爲修煉真善忍,我得以克服了舊日的沈溺與惡習;正是因爲修煉真善忍,我來到中國,用我的全部力量反對邪惡,告訴中國人民他們正在被謊言所欺騙,從而喚醒他們的正義良知;正是因爲修煉真善忍,這場迫害持續了兩年半而沒有成功;正是因爲修煉真善忍,我把自己的故事講出來與您分享。我的行動不是激進主義行動,也不是一種抗議的形式,它是一個原則性問題,是用我內心的大善大忍去證實真理的行動。
(待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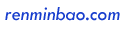

























 打印機版
打印機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