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安有一位著名的绅士韩国钧,又名紫石,前清举人出身,曾任东北外交特派员,山东和江苏省长,又曾多次主持江苏水利建设,后退休还乡。他属于国民党早期的反对党进步党,支持过袁世凯。袁死后他和国民党的高层人脉关系也很广泛。一九四○年,中共的陈毅和刘少奇都先后到过海安,称韩国钧为德高望重的政界前辈,执礼甚恭,并将海安改为“紫石县”,以表崇敬。中共在海安召开苏北临时参政会时,恭请韩国钧莅临指导。一九四二年韩国钧逝世,“紫石县”又改为“海安县”。
马氏宗祠不认我
我自幼姓马,初名马元福。后来改名马义,再后来又用了“司马璐”这个笔名从事写作,所以也有人以为我是姓司马的。我六岁时父母双亡,留下我和一位十三岁的姐姐。当时我家的住宅很大,母先逝,三个月后,父亲还未断气的时候,所有镇上和附近姓马的,都搬进我家来了。他们把我家的产业和所有贵重值钱的东西,差不多都抢光了。姓马的互相打架,无日无之。我的奶妈为了保护我,也被人打伤了。
姓马的人中也有“温和派”,在他们协商之下,留下一小部份家财给我和我的姐姐生活,并由另一家贫穷的叔叔照顾我们。我的这位叔叔待我们不错,不过,由于他的经济能力有限,我只受到两年私塾和三年小学教育,姐姐在父母去世前也读过一些书。我在十一岁时就做杂货店学徒独自谋生,也开始了我的流浪生涯。当学徒工辛苦不要紧,最难忍受的是老板和老板娘的打骂和不准我偷闲看书。有一次,老板娘骂我;“小杂种,你也配读书,给我滚出去!”
我回家把经过告诉姐姐,她哭了。我已经开始懂一点事,追问姐姐为什么哭得这么伤心?她才开始透露了我的身世。
姐姐说:“我们家本来是很富有的,父母过世以后,家产差不多都被姓马的分光了。”
我说:“那一年伯伯叔叔们在我们家抢啦,搬啦,打架啦……到底为了什么呢?”
姐姐说:“他们那些宗亲说,我们这一家姓马的‘无后’,所以凡是姓马的都可以到我们家分家,占有一份我们家的家产。”
我说:“我们不是有你和我吗?怎么可以说‘无后’呢?”
姐姐说:“我是女的,按祠堂(在封建时代的中国,祠堂的权力很大,他等于一姓的族长,有权裁决同族之间的一切纠纷)的规矩,有女没有男,就算是‘无后’了。”
未婚生子,生母自杀
我接着紧张地问:“我不是男的吗?”
姐姐看着我,迟疑了好一会,才慢吞吞地吐出五个字:“你是抱来的。”说完,姐姐转过头又哭了。
姐姐又给我看过父亲逝世时的“讣文”,在我的名字上面有“螟蛉子”三个字。在中国旧社会的伦理关系中,“螟蛉子”就是“养子”的意思。
这是姐姐第一次道出我的身世之谜。在这以前,我和别家孩子吵架时,他们都骂我“野杂种”,这时我开始悟到,他们可能早就听说过我的身世的秘密了。
我既不是马家的亲生儿子,我是从哪儿来的呢?姐姐只能告诉我:“你是从育婴堂(孤儿院)抱来的。”我问她我是怎样来到这个世界的,她就不能回答了。
我童年也和别的孩子一样贪玩,顽皮。有一晚在当地的徐春来茶叶店中,和别的小朋友捉迷藏,在追缠中扭伤臂腕,茶叶店立即请来医生治疗,也为此我和该店小老板徐展堂成了童年好友,每当他听到有人对我有侮辱性的语言,就非常气愤不平。他后来用了多年时间为我“寻根”。一九四一年冬,我一度回到海安,我们畅谈通宵,他就我的身世作了认真的查访和考证,对我讲述了以下的真情。
我的生父叫陆省文而,海安一位著名医生,生母崔氏,是海安一个大户崔家之女。陆省文而当时等于是崔家的家庭医生,常在崔家出入,把崔家小姐“诱奸成孕”,以后就生下了我。在当时的中国社会,未婚生子的少女被认为有辱家门,自己也觉得见不得人。我的生母当时还是个十七岁的少女,在忧惧中诞生了我以后,旋即吞金自杀。崔家把我送进了“育婴堂”,也全家搬出海安。不久马家就从“育婴堂”领养了我。
马家也是海安大户,有一个女儿(也就是我的姐姐),没有儿子,所以急于领养一个男孩子。我一入马家,拥有封建权威的“马氏祠堂”就紧急会商宣布,因为我不是马家人,永远不能进“马氏祠堂”。
我的马家父母实际上等于我的养父母,整日夜都双双躺在床上抽鸦片烟。由于外间传说这马家太有钱了,周围姓马的都等着这一家主人快死,后来就是我六岁时亲眼所见的,姓马的爆发一场“内战”,混战一团。
这就是我的童年时代,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我认识过的我的“家”。
父子相见,心照不宣
如果说,我的诞生,我的生母崔氏为我而自杀是一场悲剧,那么这一场马氏宗亲夺产便是一场闹剧和丑剧。我的身世中悲剧是第一幕,闹剧和丑剧是第二幕。其后我和生父见过一次面,那又是第三幕。
由于童年好友徐展堂详细谈了我的身世,所以我准备去拜祭我生母的坟墓。就在这时,不知是否有人故意作的安排,我的一位马家堂兄弟请我到他家吃饭。这一天我去了,主人说:“没有外人,都是自己家里的人。”经介绍,我的天,一位年约五十岁的中年人,竟是陆省文而先生(他虽然是我的生父,我只能这样称呼他)。我终于和他见面了,当时我笑不出,哭不出,心里很乱,外表上又要装得少年老成,若无其事,这亲父子见面的一幕,是喜是悲?是悲喜交集?是激动还是冷静?那种复杂的心情真难以形容。我们四目相对时,我很不自在。他看着我,我看着他,两对眼睛开始对话。我仔细看,我的身材和五官同他完全一样,肯定我是他这个模型中打造出来的。我心里想:“他就是我的生父,绝对没有错,我已见到生父了。”他对我谈话的态度温和,体贴,关心,不断向我碗里夹菜,嘱咐我留心身体等等,我感到他是一位仁慈的父亲。我们谈话时,彼此都没有勇气揭开这个秘密──我们的父子关系。他称我“马先生”,我称他“陆先生”。更有趣的是,他要他的孩子叫我“舅舅”。他续娶的填房也姓马,所以我们彼此的称呼都很滑稽,别人也在窃窃而笑。这一天(也可以说这一世),我们亲父子相聚三个小时,然后在“陆先生”,“马先生”的相唤中说了声“再见”。所以这一幕父子相见,勉强可说是一幕喜剧。
这次海安之行,一想到生母,我就觉得自己是个罪人,没有我,她决不会死。我又想到我的奶妈,没有她的奶水哺育我,我是活不了的。我想要哭,想要叫,我要和世界上所有的孩子一样,需要亲情,需要父母的爱。
我一生从没有见过我的生母。我来到这个世界,她走出这个世界。她付出自己青春的生命,生下我这个儿子,便和我天人永别了。陆省文而先生,你虽是我的生父,可是我一想到生母的死,我就恨你。我曾经想去生母的坟墓前痛痛快快地哭一场,后来知道她的坟墓已无影无踪了。
感怀身世,我曾写了以下几句:
吾母为吾生,吾母为吾死;
父子相逢时,心中乱如丝!
我是一个地球人
一九四一年以后,我再没有回过海安。我从此飘泊天涯,在全世界流浪了超过一个甲子(六十年)。每当朋友向我诉说他们的乡愁时,我总觉得,他们的故事,对我是很陌生的。
当我写自己的回忆录时,正在读一本英文写的传记《ANGELA'S ASHES》,作者FRANK McCOURT,曾获得普立兹奖,这本传记的卷头语是:“WHEN I LOOK BACK MY CHILDHOOD,I WONDER HOW I MANAGED TO SURVIVE AT ALL。”我一回顾我的童年就感到惊奇,我是怎样活过来的。
中国是我出生的地方,我是一个私生子,从小便是个孤儿,从小流浪。我童年的灾难,使我一辈子痛恨这个不合理的中国社会。家庭的爱,社会的爱,国家的爱,都离我很远。我在自生自灭中长大,叫我何处去寻根?又叫我何处去认祖呢?
我生来就是一个乱世中国的孤儿!
我希望现代的中国儿童不再遭遇像我一样的悲惨命运。我是在那样一个社会环境下逐步成为一个左倾少年的。
我现在作为一棵野生植物,活得自由自在。
我现在是一个自由人,我属于这个世界,我也拥抱这个世界。
我现在是一个地球人,我的国籍是“地球”,这个地球任我逍遥!待我不薄!
我默默地祈祷,我的生母能“复活”……但是,这不过是一个游子的梦,永远不可能成为事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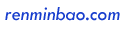


























 打印机版
打印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