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夜,你們不在我的身邊,即便是你們在我身邊的時候你們也從不知道我在做些什麼,無論你們在不在我的身邊,我都清楚你們在做些什麼。你們永遠開着無牌照的車,你們從來不敢表明你們的身份,你們從不願讓人甚至不讓家人知道你們是什麼,在做什麼,在與我相處的日子裏,你們中大多數人的那種時時刻刻擔心看不到我的存在,卻又時時刻刻懼怕我看見你們的矛盾心理驅使下的行爲貫穿了始終!
20日,在你們羣車的「護送」下我進入河北省,踏上返鄉的路程。我的日子裏有沒有你們,無疑都不會改變我做事的習慣和方式,當然在你們也沒有了我的日子裏,你們也不會因此而改變自己任人擺佈,不得不馴服的被永遠躲在你們背後的人差使的命運。對你們而言,盯守是不變的,偶爾改變的只是不同的盯守對像而已,諸如它是高智晟,還是郭飛熊。
在有你們的日子裏,你們面對我時所表現出的超乎常人想像的緊張和煞有介事的如臨大敵狀,表明躲在你們背後者的眼裏,高智晟是個超極危險人物。在你們圍堵我全家的85天裏,你們的那種對我們全家跟蹤的寸步不離及目不轉睛,持續營造着我的「危險」及你們的「高度責任」,你們有沒有或者說你們應當思考一個非常簡單的道理,即;元月20 日後發生了什麼樣的事件突然改變了我在你們背後操縱者眼裏的危險,這「危險」是怎麼突然在這一天後就不存在了呢?我離開北京時,不同線上(你們的行話)的九輛車「護送」我出京,意在營造我的「危險」程度,不料兩小時後進入河北省的一段路程後,我的「危險」嘎然而去,這種狀態的極不正常足令我們尋味。
今天,你們不再盯着我,較你們盯着我的日子沒有發生任何變化,社會的「和諧」依舊,江山的「安穩」如常,曾與類華萊氏般的大人物「談笑風生」的、同樣也屬大人物者依舊可以着談笑風生,足見盯守跟蹤我是沒有多少道理的。
在和你們「相處」的日子裏,你們中間的個別人持續的、刻意的、不甚友好的針對我及家人做過一些讓人痛心的事,直到元月21號、22號兩天,你們中間的個別人也還五次打電話用人世間最不文明的語言謾駡我及我的早已逝去的父母,但你們中間任何個體都不是我的敵人,一則,我沒有敵人,更不會去尋找敵人。另則,我們作爲個體之間產生恩怨的基礎條件全無,儘管這兩天對你們中的個別人持續地在電話中對我及我母親不堪入耳的謾駡讓人持續地痛心着,這種痛心多是對你們如此糟賤自己,不別皁白的服從着毒化你們自己的人性、道德及善良的安排,實實令人扼腕嘆息!你們中的每個人無疑都有着受過高等教育的經歷,個別年輕人爲什麼會淪落到不若市井潑婦,你們怎麼會接受用最下流的語言辱駡他人,且是持續地辱駡他人這種「工作」安排呢?怎麼能喪失了對人自我行爲認識的能力呢?
阿倫特在《極權主義起源》裏說過:「極權政體的弊害之一,是被統治的人民民智日趨低愚,即使豐衣足食,極權統治下的人民充其量是一批腦滿腸肥的白癡與馴順聽命的木偶而已。」我無意以此來喻意那些祕密警察兄弟,但極權體制下的每一個人,你無需趨就之,只要你未去堅拒之,有幾個人能擺脫成爲「白癡與馴服聽命的木偶」的命運呢。
2006年元月23日於陝北佳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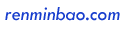































 打印機版
打印機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