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紅英和王杉在學校裏是公認的模範夫妻,自修煉法輪功後,兩人更是處處先爲他人着想,助人爲樂。教學之餘,紅英和王杉利用學校寬闊的操場引導附近的五十多個人學法煉功,其中有二十多個是學校的教職員工,因此而深得佳譽。紅英在教學上更加勤奮,她把法輪功真善忍的道理溶入對學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並與日常教學相結合,又以身作則,身體力行,受到學生由衷的敬佩。日久天長,學生們養成了良好的習慣,不論在學校還是在家裏,都自覺以真善忍要求自己,努力學習,尊老愛幼,助人爲樂,爭做好人。使全校的學風和校風煥然一新。尤其是家長們看到自己孩子驚喜的變化,紛紛給學校來信或口頭向校長反映:「一定要給何紅英老師記功授獎!」
一九九七年年底,經教育系統舉薦,紅英被評選爲全市十大傑出青年之一。
......
公元一九九九年七月中旬,紅英到省城參加「全省先進教師經驗交流會」,並在會上作了重點經驗介紹。七月二十日,與會人員突然接到通知:下午休會。統一列席參加省教委機關全體人員緊急會議,有重要通知。
省教委禮堂的主席臺上沒有任何領導就坐,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大型背投電視。一名工作人員正在調試準備。
下午四時正,中央電視臺新聞節目振聾發聵地播出了「中共中央關於取締法輪功的決定......」。
臺下的紅英象突然遇到了魅魘似的,心裏作堵,欲說難言,兩顆清淚在眼簾裏晶瑩欲滴......怎麼會這樣呢?中央四月份通告中,不是說得好好的麼?「人民有選擇任何功法鍛鍊健身的自由......中央決不會干涉這一自由……也不要聽信任何謠言!」可如今,短短三個月的時間,怎麼出爾反爾地兌現了「謠言」呢?!堂堂中央,怎麼會言而無信呢?!......散會後,紅英木訥訥地隨着人流回到住宿的房間。關住房門,淚水潸然而下。
三天後,紅英回到了縣城。
等待着她的是一場更加意想不到的不幸。校長親自到車站接紅英回學校,一路無語,面色凝重。紅英預感到將有什麼事情要發生。
在校長辦公室裏,校長沒有象往常那樣坐在辦公桌內側的圈椅裏,而是與紅英面對面坐在相隔一張茶几的沙發上。
「咳!......」校長嘆了一口氣,欲言又止。
「校長,」紅英說,「不論發生什麼事情,我都能理解,您就說吧。」
年過半百的校長眼簾溼潤了。
「紅英啊,天有不測風雲......」
原來,就在中央電視臺播出重要新聞的當天,全國公安同時採取了行動,警車穿街堵巷,晝夜鳴笛。各地法輪功輔導站、點的負責人和骨幹人員紛紛被劫持抓捕。縣城也不例外,當天就抓捕了二十多名法輪功主要骨幹,僅縣機械廠一次就抓捕了五人,連「新長征突擊手」陳力也被逮捕了。紅英爸爸於當天下午被幾個警察強行帶到公安局,晚上被關進了看守所;媽媽被強制監控,不準外出,一個人摟着外孫默默流淚。王杉得知情況後,與次日上午到公安局講理,要求放人。公安局的警察獰笑着說:「嘿嘿,還有敢找上門來的?正說抓得不夠呢?」王杉也被關進了看守所。
「紅英啊,」校長接着說,「你要有個思想準備,縣委通知說,你現在是省、市教育系統的先進典型,考慮到社會影響,暫時不採取強制措施,但教育局和學校必須全面負責擔保,不準外出,不準與任何法輪功的人聯繫;等候通知,要在電視上公開表態與法輪功決裂,還要揭批......」
「校長,別再說了,」紅英眼中的淚水奪眶而出,「我的爲人你知道,我決不可能昧着良心去揭批我的師父!」
「紅英啊,」校長拭去眼角的淚,「我和你爸是老相識,我一直把你看成孩子,你的爲人我更清楚,我心裏也難受啊!可是,現在的形勢,你頂不住啊!……在咱中國,凡是中央最高領導決定要批判,要鎮壓的,說你是什麼就是什麼……你現在只能委曲求全,留得青山在,不愁沒柴燒啊!」
「校長,您的心意我都明白,」紅英誠摯而又認真地說,「我知道你都是爲我好。但,法輪功確實沒有錯!不論對個人還是社會都只有好處。鎮壓法輪功,不會是中央的集體意願,一定是個別人指鹿爲馬!這個冤案一定會澄清的!......不管怎麼說,我堅持正義,決不會扭曲人格去妥協!」
......
(七)
由於紅英堅持不配合,被勒令停職檢查,檢查期間負責打掃衛生;據說,這也是校長出面一再說情和擔保後的照顧了。叫監控上班。
爸爸和王杉一直被關押在看守所。上面有規定,法輪功犯人一律不讓家裏人探視。據公安人員傳話說,兩人的態度都不好,爸爸是一言不發;王杉是口口聲聲大講法輪大法好。目前都屬於嚴管犯人。
紅英被監控上班,要保證24小時隨叫隨到,不準離開縣城。只能回家照顧孩子。
媽媽爲爸爸和王杉擔心,也爲大法突然遭到如此嚴重的迫害而憂心忡忡,一想這些就流淚。紅英安慰媽媽說:「爸爸心胸寬,想得開,難不住他。王杉年輕,在裏面吃點苦也沒啥。您就放心吧!」紅英想,現在爸爸和王杉都不在,自己要成爲媽媽的主心骨。「媽,師父教育咱講真善忍,做好人,做更好更好的人……這到全世界那裏都沒有錯!天理昭昭,這冤情遲早會大白於天下的。不管遇到什麼困難和危險,咱堅持真理,堅信大法的心都不能變啊!」
媽媽含淚點點頭,「這我知道,可就是一想這冤情,淚水就忍不住了。」
......
一天又一天;一月復一月。
秋風吹盡了黃花;寒風送來了白雪。
在連續半年多的時間裏,中央電視臺新聞聯播中,每天都利用大量時間連篇累牘地對法輪功進行批判。可是,批判的日子久了,人們發現,除了給法輪功亂扣帽子,逐步升級,從「非法組織」到「邪教」之外,並沒有真正找到法輪功人員危害社會的哪怕一丁點「壞人壞事」。這就奇怪了?……究竟是誰得了精神病?
於是,中央電視臺新聞聯播節目的收視率降到了開播以來的最底點。一到晚七點,家家戶戶都嚷道:「關機,關機;別看了,浪費電!」
.......
就在這年第一場雪花紛紛揚揚的時候,傳來一個令人震驚的消息:機械廠的陳力,在被關押期間突發心臟病去世了……!誰都不相信,誰又都無可奈何!
日子真難捱啊……
臘月裏一個寒風刺骨的日子。公安局突然通知,讓紅英帶一萬元擔保押金,去接王杉保外就醫。紅英又喜又怕,喜的是丈夫終於出來了,怕的是「保外就醫」?丈夫究竟怎麼了?
學校的老師們聞訊後,悄悄地很快湊足了錢,交給紅英。
王杉是被用擔架抬進媽媽家的。他渾身是傷,右腿裹着石膏筒。
等人都走了以後,紅英緊緊握着王杉的手,淚水一顆又一顆落在丈夫胸脯上,打溼了那件漬滿血污的襯衣。
晚上,王杉將關押期間的遭遇告訴了紅英和媽媽。
「縣公安局主管法輪功案件的幹警中,有幾個爲首的人天良喪盡,他們對關押的法輪功人員百般折磨,坐飛機、坐老虎凳、吊打、腳踢、電警棒……機械廠的陳力,就是讓他們給活活打死的,根本就沒有心臟病……他們之所以這般肆無忌憚,喪心病狂,主要是吃透了中央的政治精神,打了白打,打得越賣力表現越好,打死了就隨便找個藉口,不會受到任何追究。爲首的頭頭還因此得到獎勵……現在更加變本加厲……爸爸一直不開口說話,也不給他們頂嘴,年齡也大了,總算沒有太受苦……現在被關押的50多個人,多數都被他們打的傷痕累累,慘不忍睹……」
媽媽在一旁不停地抹淚。紅英眼中的淚水漸漸地化成了聖潔的火光。她心裏暗暗發誓:“這些惡魔的可恥行徑,一定要讓全社會的人們都知道!
(八)
二零零零年的春天姍姍來遲,樹上的花兒也開的稀稀落落。華北平原上颳起了老人們從沒見過的沙塵暴,一場接一場,北風呼嘯,天空一片渾黃,飛沙眯得人睜不開眼睛。街巷裏的孩子們在傳唱一支童謠:
天上落沙地上哀,
春天桃花秋天開;
忽冷忽熱快回家!
江中妖怪上岸來。
......
經過幾個月的療養,王杉的身體基本上恢復了,只是右腿膝部傷損較重,治療太遲,走路還有點一拐一拐的。
縣城的街巷裏開始出現法輪功傳單,人們議論紛紛:
「煉法輪功的人可都是好人啊!」
「機械廠的先進工作者陳力,是被公安局的警察活活給打死的!」
「國家鎮壓法輪功,冤枉啊!」
一天傍晚,紅英下班後騎車回家。一輛自行車趕上來與紅英並行,騎車人也是個年輕女子,扭臉朝紅英一笑,輕聲說:「何姐,我是功友。你家的遭遇我們都知道,都很敬佩!現在大家都堅持修煉,有上北京的,也有散發傳單的,誰都不怕!讓那些黑了心的警察抓吧!他們永遠抓不完!……你有啥事就找我,我叫清芬,就住在這條小巷西邊第三家。」說完朝紅英又一笑,輕靈地拐彎進了一條小巷。
紅英回到家,將路上遇到的情況高興地向王杉說了一遍。兩人目光相對,會心的菀爾一笑。原來,縣城裏散發和張貼的傳單中,有不少是紅英和王杉撰寫的。王杉有一個外人不知道的特長,左右手都能寫一筆好字,但字跡不同。自從王杉保外就醫以後,紅英和他就不斷商量,眼看讓邪惡恐怖着的形勢,電視和報紙上全是顛倒黑白的謊言。正所謂「假話重複三遍,也讓人信以爲真。」整天喋喋不休的造勢宣傳,着實矇蔽了一大批不了解法輪功的人們。紅英和王杉以及媽媽都是看在眼裏,急在心裏。這些被矇蔽了的人們,如同被險惡的騙子矇住眼睛帶到了懸崖邊上……一定要讓他們了解是非真相!把矇住眼睛的黑布揭開!然而現在唯一能做到的,就是把法輪功的真實情況以及被迫害的真相寫成傳單,通過散發和張貼告訴世人。於是,在王杉療養治傷的同時,每每深夜,紅英和王杉奮筆起草,定稿後由王杉左手書寫,書寫完由媽媽連夜送出去,媽媽散發一部分,也讓其他功友分別散發和張貼。
「看來,」王杉興奮地說,「只要我們堅持向人們講清真相,形勢一定會好轉!」
「是啊,」紅英說,「下一步,我們還要再擴大範圍,讓更多的人了解法輪功被迫害的真相!」
兩人的手不約而同地緊緊握在一起,兩顆炙熱的心在怦怦跳動。
(九)
悲唳南飛的大雁,送來了秋的蕭瑟。在看守所被無辜關押了一年多的爸爸,被宣判勞教三年,送到市裏的勞教所。勞教是××黨專政的特殊工具,不需法院立案,也不必履行任何法律程序。只要公安局開出一張「勞動教養通知書」,籤不簽字都強制執行。
媽媽聽說後靜默了片刻,眼中的淚花晶瑩地掛着,沒有流出來。走過這一年多的風吹雨打之路,媽媽硬朗多了。她知道無辜的丈夫是在爲捍衛真理而承受魔難,應該爲他而驕傲!
一個秋雨霏霏、冷風陣陣的傍晚。紅英從學校騎車回家,遠遠地就看見清芬一邊張望一邊迎着自己走來。來到跟前她下了車,清芬打着傘靠近她,小聲說:「有個緊急事,×××自心生魔,叛變啦;一直向公安局舉報告密!抓走好幾個功友啦!千萬要小心她!」紅英心裏一震,「好,你放心吧!」
紅英加快車速,不一會到了家。急忙把這一消息告訴了王杉和媽媽。
「不好!」王杉說,「咱倆寫傳單的事這個人知道。」
紅英冷靜地點點頭。
媽媽說:「我下午上街回來時,有輛警車停在附近,裏面的人一直盯着咱的門口看。」
「看來,」紅英一邊思索一邊鎮靜地說,「他們一定會來抓人,與其讓他們抓走,不如索性……」紅英欲言又止,不由得把目光投向了媽媽。
此刻,蒼老的媽媽那溼潤的目光彷彿凝固般地望着門外秋雨瀟瀟的遠方。五歲多的小剛提前懂事了,見大人在說重要的事,依偎在姥姥身邊,牽着姥姥的衣襟,一動也不動。
一家人同時靜默在那裏。
須臾,媽媽的目光從陰霾沉沉的遠方緩緩收回,落在女兒目光依依的面龐上。
「小風啊!……」媽媽的聲音有些顫抖。
「這天?咋老是不晴啊!」
兩汪淚水從媽媽佈滿皺紋的臉頰上驟然滑落。
紅英不由得象兒時一樣依偎到媽媽懷裏,「媽!」一邊喊一邊摟緊了媽媽。
媽媽抬起右手,也象二十多年前一樣,輕輕地撫摩着女兒的柔發。眼淚一顆又一顆,滾落在女兒的髮際。
「媽,」王杉說,「事不宜遲,我們今晚就動身。」
(待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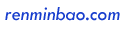



























 打印機版
打印機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