慘劇的罪魁禍首是冷漠。長久以來,冷漠在我們的文化體系中被讚揚爲「堅強」和「勇敢」,從很小的時候起,我們就被要求成爲「特殊材料」製造成的人。我不想過多地譴責那個不通人情的警察,因爲他本人也是這一整套制度與文化的犧牲品。他不會感到自己做錯了什麼,反倒會爲自己的「忠於職守」而洋洋得意。是我們共同製造了一種以冷漠爲「光榮」、以冷漠爲「進步」的社會氛圍。我們以爲自己在突飛猛進,其實我們依然在野蠻地茹毛飲血,我們的精神世界是一片荒蕪的、一無所有的曠野。我在王朔的小說中,讀到軍隊大院裏的孩子用磚頭砸別人腦袋時的快樂。年輕的打手們是不會害怕鮮血的,他們對生命也沒有絲毫的敬畏之感。而作者對這種嗜血的冷酷顯然充滿了讚美和欣賞。我在餘華的小說中,也讀到殺人者與被殺者快意,殘酷的殺戮成了作家案頭把玩的小擺設。餘華曾經在一次訪談中說,小時候家住停屍房的對面,夏天常常到涼快的停屍間睡午覺,由此獲得了無窮的靈感。我在香港著名導演吳宇森的若干電影中,更是發現了一種推展到極致的「暴力美學」。殺戮行爲越多的主人公,最後必然成爲讓人尊敬的英雄。誰要是心慈手軟,誰立即就被「物競天擇」的江湖原則所淘汰。我們閱讀著這樣的小說、觀賞著這樣的電影,並冷靜地耳聞目睹著身邊一幕幕的慘劇,我們早已經司空見慣。他人的苦難不足以成爲自身的苦難,「愛」成爲一種長期缺席的元素。我們的心靈就像是一片逐步被沙化的綠洲,再也蘊含不了一點點甘泉,就連堅韌的仙人掌也無法存活。冷漠的盡頭是麻木,我想起了作家盧躍剛在《大國寡民》中說過一句話:「貧窮和愚昧並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冷漠和麻木。」
經歷過「文革」的中國人,由血腥走向覺醒和反思乃至懺悔的,畢竟是其中的極少數。絕大多數的人,卻在血腥中變得冷漠和麻木,他們拒絕懺悔和反思,他們毅然選擇逃避和掩飾。如何對待歷史,其實也就是如何對待現實,這兩者是相通的。不肯面對歷史的苦難的人,同樣也不肯面對現實的苦難。他們不把冷漠看著一種罪惡,反而將其當成是一種令人羨慕的生存策略。東方發生在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正在被迅速地遺忘和改寫,而西方發生在三四十年代的納粹暴政,卻越來越被凸現和批判。
任何閱讀過《拉貝日記》的人,任何親身到過奧斯維辛集中營的人,都會被那些恐怖的場面所震撼。在德國,集中營已經成爲紀念館,成爲民族記憶中一道永遠的疤痕。在一間陰森的地下室裏,裝滿小孩們玩具的箱子被細心地碼在一起,堆積如山,至今好像仍在等待它們的小主人們來著最後的挑選。在許多小箱子上,用粉筆寫著「麗貝卡」、「伊斯爾」、「伊莎克」等成千上萬個無辜的孩子和家庭的名字,全都清晰可見,而這些人都被暴徒們趕進了煤氣殺人室。瑞士法學家托馬斯極接□オb《人權是什麼》一書中指出:「這種野蠻的行爲永遠也不可能得到全面的解釋。許多犯下過這種罪行的人爲自己辯護說,它們的受害人不是人,只是老鼠之類的害蟲,應當趕盡殺絕。他們把我們帶到幕後的真正策劃者那裏。這些策劃者想證明,人類劃分爲若干不同的等級,應當根據其種族、宗教、民族和語言身份而區別對待。那個不承認人在原則上具有平等的權利並具有同等的價值的人,那個通過新聞媒介和其他宣傳方式散佈諸如『無教養』之類說法的人,那個附帶地煽動仇恨其他民族的火焰的人,那個製造恐怖的人,要對那些把人領進煤氣殺人室的暴徒們承擔一份責任。」他的論述已經超越了一個普通的法學家的眼界。
今天的冷漠實際上來自於不肯承擔昨天的責任。孱弱的文人學者,如週一良、浩然、餘秋雨等人是如此,比他們更應當承擔責任的幕後策劃者和前臺打手們更是如此。全民共懺悔的呼籲,直到今天還是被當作笑話,並遭到聰明人的圍剿。在我們這裏,建立「文革博物館」的呼籲,一直是阻力重重。對歷史的掩蓋,直接導致了現實社會生態的惡化;對責任的躲避,直接帶來了冷漠心態的大面積擴散。我無法忘懷那個產婦和那個嬰兒悲慘的死亡,他們的生命融匯進了歷史上無數的、無辜的冤魂的行列。是冷漠殺害了他們。托馬斯極接□サN「罪」的定義擴充開去,闡明了冷漠本身就是罪惡的道理:“無數冷漠的、不準備爲人類的尊嚴和人權而站出來的人也應當承擔連帶責任。這些冷漠的人既不在國內也不在國外抗議1935年頒佈的紐倫堡法律,那就是衆所周知的決定對猶太人給予最可怕的歧視就侮辱的法律;當瑞士外交官同德國代表就德國猶太人的護照加蓋猶太標記達成協議(瑞士當局以此防止德國的猶太人逃入瑞士)時,這些冷漠的人沒有集合起來進行抵抗。在30年代,當意大利法西斯政權要求教授們向法西斯主義宣誓,保證教育學生成爲法西斯意大利的忠實成員時,3000名教授中只有大約0.5%的人拒絕宣誓。例如,天主教教堂的藉口是含糊不清的:法西斯主義應當就是意大利國家,自欺欺人,還證明其簽署文件的行爲是正當的。這些冷漠的人耽心的只是自己的生計,他們構成了爲獨裁者和民族仇恨煽動者鋪下的紅地毯的表層。”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除了少數的抗議者,我們這「沉默的大多數」、「懦弱的大多數」都是有罪的,因爲沉默、懦弱、冷漠和麻木本身就是一種嚴重的罪行。我們曾經沉默、曾經懦弱、曾經冷漠、曾經麻木,今天我們在面對包括那個產婦和那個嬰兒在內的一個個消逝的生命時,我們依舊會沉默、依舊會懦弱、依舊會冷漠、依舊會麻木。
冷漠是一種特殊的罪惡。只有意識到了這一點,我們才有可能與之作艱鉅的抗爭,我們才有可能企盼愛、同情、憐憫這些珍貴的情感的降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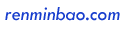






























 打印機版
打印機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