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1977年3月5日,在斯大林逝世的週年紀念日裏,雷賓找到了幾個過去斯大林衛隊的工作人員,他們在斯大林逝世時都在近郊別墅工作。
根據這些保衛人員(名義上他們被稱爲「完成斯大林委託的工作人員」)的敘述,雷賓記錄下了一些證詞。
開始是一般情況:「2月28日夜裏,政治局委員們在克里姆林宮中看電影。看完電影后,他們驅車前往別墅。到斯大林別墅去的有貝利亞、赫魯曉夫、馬林科夫和布爾加寧。他們在別墅一直呆到清晨4點鐘。那天在斯大林處值班的是高級工作人員斯塔羅斯京和他的助手圖可夫。別墅警衛長奧爾洛夫那天休假,值班的是他的助手帕維爾·洛茲加喬夫……」
當天在別墅中的還有被服管理員布圖索娃。
客人走了以後,斯大林就躺下睡覺了。此後就再也沒從自己的房間裏走出來。
除了一般情況外,雷賓還單獨記錄了保衛人員斯塔羅斯京、圖可夫和洛茲加喬夫的證詞。斯塔羅斯京的證詞最爲簡短:「從19點鐘起,我們開始爲斯大林房間中的寂靜感到不安……在沒有召喚的情況下,我們倆個(即斯塔羅斯京和圖可夫)都不敢擅自進入斯大林的房間。」
他們叫洛茲加喬夫進去看。於是,帕維爾·洛茲加喬夫就成了第一個看見斯大林躺在桌旁地板上的人。
根據圖可夫和洛茲加喬夫的敘述所記錄下的證詞,已讓我感到奇怪:爲什麼斯塔羅斯京在敘述經過時沒有說到一個令人驚訝的細節:斯大林在躺下睡覺之前給衛隊下了一個叫人難以置信的命令。
保衛人員圖可夫說:「客人走了以後,斯大林對僕人和警衛們說:『我要睡了,不會再叫你們的,你們也可以去睡了。』」。圖可夫強調:「過去斯大林從來沒有下過這樣的命令。」
就這樣,一向極爲重視安全工作的「當家的」,突然破天荒地命令自己的警衛員們去睡覺,實際上讓自己的幾個房間處於無人保衛的狀況。而就在這天夜裏,他中了風!!
在主要見證人(即第一個看見斯大林中風之後躺在地上的洛茲加喬夫)的證詞中,我也讀到了同樣的細節:「斯大林說:我要睡了,你們也都去睡吧……」
「我不記得,」洛茲加喬夫說,「從前什麼時候斯大林曾下過『大家都去睡覺』的命令。」
於是,我決定去採訪洛茲加喬夫。
主要見證人
我開始追蹤彼得·瓦西裏耶維奇·洛茲加喬夫。我給他打了許多次電話,準確地說,足有幾十次。他一直猶猶豫豫,拖着不想見我。他們直到進墳墓都會感到害怕:他們被指定爲之服務的那位「祕密對象」(他們彼此就戲稱爲「被指定者」),依然像以前那樣統治着他們。然而我不屈不撓的精神終於戰勝了:洛茲加喬夫總算同意和我會見了。
在克雷拉特新建區他那小小的住宅裏,坐在窄小的廚房內,我記下了他的證詞。
在謄清了記錄、並用打字機打好之後,我再次拜訪了他,請他在主要的章節上簽字。
這一次他出奇得痛快:戴上厚玻璃眼鏡,長時間地讀着記錄,然後用顫抖的手在每頁記錄的下面簽了字。
「當家的」的最後一夜,是誰下的命令?
終於,洛茲加喬夫講到了那一夜:“3月1日的前一天夜裏,我在別墅值班……警衛長奧爾洛夫剛休假回來,那天是他的休息日。在斯大林那兒值班的有高級工作人員斯塔羅斯京、他的助手圖可夫、我和馬特廖娜·布圖索娃。那天夜裏『客人們』要來——『當家的』這樣稱呼常到他這兒來的政治局委員們。像往常一樣,客人們要來時,我們和『當家的』一起制定菜單。2月28日那天夜裏,我們在菜單中有「馬紮裏」牌葡萄汁,我記得是三瓶。「馬紮裏」是一種年代不久的葡萄酒,因爲度數不高,『當家的』就叫它葡萄汁。那天夜裏『當家的』把我叫去吩咐:『給我們每人來兩瓶葡萄汁』……那天夜裏都有誰來了?都是常客:貝利亞、馬林科夫、赫魯曉夫和大鬍子的布爾加寧。過了一陣子,『當家的』又叫:『再來點葡萄汁』。又送上了。一切都好,他沒提什麼意見。後來就到了清晨4點鐘……快到5點的時候,我們給客人們備好了汽車。『當家的』送客時,警衛也跟着送,爲的是客人走後好關門。當警衛員伊萬·瓦西裏耶維奇·赫魯斯塔廖夫關好了門時,他看見了『當家的』。『當家的』對他說:『睡覺吧,你們都睡去吧!我這兒不需要什麼了,我也要睡了,今天我不需要你們了。』
「赫魯斯塔廖夫跑來高興地說:『嘿,小夥子們,從來還沒下過這樣的命令……』說着他向我們傳達了『當家的』說的話。」說到這裏,洛茲加喬夫補充說:「是真的,我在別墅工作了那麼多時候,『當家的』說『睡覺去吧』,這還是僅有的一次。平常他只是問:『想睡覺麼?』然後用眼睛把你從腳到頭狠狠地看一遍,像要看穿了似的。呶,哪兒還敢想睡覺呀!接到這個指示,我們當然很滿意,就大膽地躺下睡了。」
「等一下」,我問他,「怎麼又出來一個赫魯斯塔廖夫?您過去沒說過這個赫魯斯塔廖夫也在別墅裏啊!」
洛茲加喬夫說:「警衛員赫魯斯塔廖夫在別墅只呆到早上10點鐘,以後他就回家休息了。替換他的是斯塔羅斯京,米哈伊爾·加夫裏洛維奇。」
(這就是爲什麼斯塔羅斯京沒告訴雷賓關於「當家的」曾下達一個奇怪命令的原因:他本來就沒聽見這個命令。——作者)
總之,那天夜晚他們在近郊別墅只喝了些溫和的葡萄酒,沒喝白蘭地,也沒喝任何可能引發病症的烈性酒。據洛茲加喬夫的敘述,「當家的」那天「很和氣」。如果他感覺身體不適,「他的心情就會很糟,那時你最好別惹他,」——洛茲加喬夫這樣說。
但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那句令人吃驚的話:「你們都睡去吧」,這樣的話洛茲加喬夫還是第一次從「當家的」那兒聽到。
準確地說,他不是從「當家的」嘴裏聽到,而是從警衛員赫魯斯塔廖夫的嘴裏聽到的。是赫魯斯塔廖夫傳達了「當家的」的命令,然後在早上就離開了別墅。這個命令讓洛茲加喬夫和另一個警衛員圖可夫感到吃驚,因爲「當家的」一向極嚴格地要求遵守秩序。
然而那句話破壞了神聖的秩序:允許他們大家都去睡覺,那就是說允許不守衛他的房間,允許他們不彼此監視。
於是,就出事了。
洛茲加喬夫說:「次日是星期天。早晨10點鐘,像往常一樣,我們都聚在廚房裏,開始安排當天的工作。」
是的,因爲有了命令,洛茲加喬夫就放心地睡到了上午10點鐘。很自然,他不知道他的同伴們在夜間都幹了些什麼。比如說,那個傳達了「當家的」那難以置信的命令之後,過了夜就回家去了的赫魯斯塔廖夫,他幹了些什麼?
洛茲加喬夫接着說:“到了10點鐘,斯大林的幾個房間裏『還沒有動靜』(我們就用這句話表示他在睡覺)。11點鐘了,仍沒有動靜,12點鐘時,還是沒有動靜。這已經奇怪了:平常他在11點到12點鐘左右起床,有的時候甚至10點鐘時他就不睡了。
“已經到了中午1點,還沒動靜。兩點鐘了,那幾個房間裏仍是沒有動靜。到了3—4點鐘,依然沒有任何動靜。可能有人給他打過電話,但是在他睡覺時,電話就接到別的房間裏去。我和斯塔羅斯京坐着。斯塔羅斯京說:『有點不對勁兒,咱們怎麼辦?』『是真的,怎麼辦呢?到他房裏去?』可是他非常嚴格地規定:如果他房中『沒有動靜』,決不允許別人進去,否則嚴懲不貸。我們倆個就這麼坐在辦公樓裏,這樓由25米長的走廊與斯大林的幾個房間相聯,有單獨的門通向那裏。已經6點鐘了,我們仍然不知所措。忽然,站崗的勤務兵從街上喊:『我看見有燈光了,在小飯廳裏。』感謝上帝!我們心想:一切都好了。此時大家都各就各位,大家都時刻準備着,慌忙地跑來跑去。8點鐘了,仍是啥動靜也沒有。我們不知如何是好。9點了,沒有動靜,10點了,還是沒有!我對斯塔羅斯京說:『你去看看,你是衛隊長,你應該想點辦法。』他說:『我害怕。』我說『你害怕,難道我是英雄?我應該到他那兒去嗎?』正在這時,信使來送郵件了,有黨中央來的一包文件。文件平常由我們,準確地說,由我去送給他。送文件——是我的責任。『有啥辦法呢,』我說,『我去吧!萬一有個三長兩短,弟兄們,你們可別忘了我。』是啊,就該我去。
平時我們進他的房間,完全用不着悄悄地走。有時,還要故意地大聲把門碰上,爲的是讓他知道有人來了。要是有誰輕輕朝他走去,他就會有十分病態的反應。你應該大踏步地進去,在他面前不要不好意思,也不要挺身直立,不然他就會對你說:『幹什麼你在我面前直挺挺的,像個好兵帥克?』”
“呶,我打開了門,大聲地在走廊裏走着。我們平常送文件去的那間房子,恰好是在小飯廳的對面。小飯廳的門正開着,我朝裏面望去,看見『當家的』在地上躺着,右手是抬起來的……就這樣(洛茲加喬夫說到這兒,把半彎曲的手臂稍微抬起。)我整個地驚呆了,手腳都不聽使喚了。當時他大概還沒失去知覺,不過已經不能說話了。他的聽力很好,大概是聽到了我的腳步聲,他費力地抬起手來,可能是向我求助。我跑到他身邊問:『斯大林同志,您怎麼了?』他在這段時間裏尿溼了衣褲,自己想用左手整理一下。我問他:『是不是去請醫生?』他含糊不清地回答:『滋……滋』,說不出別的來。地板上扔着一塊懷表,還有《真理報》。我把表拾起來看,時針指着6點半。這是6點半鐘發生的事。我記得,桌子上有一瓶『納爾贊』牌礦泉水。房子裏燈亮了的時候,他可能是去拿礦泉水的。我問了他大概有兩三分鐘,忽然他輕聲打起呼嚕來……聽見這輕輕的呼聲,你會以爲這人睡着了。我抓起了電話筒,發着抖,淌着冷汗,打電話給斯塔羅斯京:『快到我這兒,快來。』斯塔羅斯京來了,也嚇得慌了神。『當家的』仍是沒有知覺。我說:咱們把他抬到沙發上去吧,在地上不合適。在斯塔羅斯京之後,圖可夫和布圖索娃也來了。我們大家把他抬到了沙發上,躺在地上不合適。我對斯塔羅斯京說:『去給大家打電話,一個也別例外。』他去打電話了。我一步也沒離開『當家的』,他躺在那兒,一動也不動,只是打着呼。斯塔羅斯京打電話到克格勃,找伊格納季耶夫。後者嚇壞了,讓打電話給貝利亞和馬林科夫。在斯塔羅斯京打電話的時候,我們幾個商量了一下,決定把『當家的』抬到大飯廳的大沙發上去,因爲那兒通風好。我們大家一起把他抬了過去,放在沙發床上,給他蓋上了毛毯。看來,他凍得夠嗆,從晚上7點就躺在地上沒人管。布圖索娃幫他把襯衫的袖子整理好,他大概非常冷。這時候,斯塔羅斯京給馬林科夫打通了電話。過了半小時左右,馬林科夫打來電話說:「我沒找到貝利亞。」又過了半小時,貝利亞來電話吩咐:「關於斯大林同志生病的事,對誰都不要說。」
就這樣,又過了一個小時,沒有人來看望垂死的斯大林──過去的「當家的」。
只有「被指定爲他服務的人員」坐在他的床邊,等待着上級的指示。
「是我幹掉了他」
洛茲加喬夫說:「我又剩下了獨自一人。我想,還得把斯塔羅斯京叫來,讓他仍然去叫他們。我說:『否則他要是死了,我和你都要掉腦袋。快去打電話,叫他們來。』」
洛茲加喬夫說:「第二天早晨7點多鐘,赫魯曉夫來了。赫魯曉夫問:『當家的』怎麼樣了?我回答:『很不好,他的確出了問題。』赫魯曉夫說:『醫生馬上就到。』」
「我心想:感謝上帝。8點半到9點鐘之間,醫生們到了。」(這是在沒人救護的情況下他躺了13小時之後的事!)
我們永遠不可能知道,那天夜裏在「當家的」那幾間關着的房間裏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但只有兩種可能:
或者是「當家的」胡塗了,真的讓大家都去睡覺,而夜裏他中了風;
或者是赫魯斯塔廖夫受了什麼人的指使,讓服務人員都去睡覺,爲的是自己,或某個我們還不清楚的人物能與「當家的」單獨在一起。
在弗拉西克被捕以後,貝利亞當然會在已無人監視的斯大林的衛隊中收買爲自己辦事的人。「當家的」認爲貝利亞微不足道,可是他錯了。貝利亞要利用最後一次機會,爭取自己能活下來。
是赫魯斯塔廖夫自己潛入了斯大林的房間,還是另外有一個人?是否他們在「當家的」喝過「馬紮裏」酒後昏昏入睡之際給他打了針?是否這針劑就引起了中風?是否「當家的」在感到不適之後仍然醒了過來,並掙扎着試圖呼救?是否藥針起了作用,他只能勉強走到桌旁?如果情況的確如此,那就可以理解爲什麼戰友們竟如此膽大包天:在知道出事了以後,仍然不急於前往救護。似乎他們早就知道出了什麼事,知道「當家的」對他們不構成危險。
就算是第一種情況,四位戰友也是心安理得地、有意識地丟下了斯大林,讓他無助地死去。所以,在兩種可能的情況下,都是他們殺死了他。
所以,貝利亞有理由對莫洛托夫承認:「是我幹掉了他。」此話後來莫洛托夫向丘耶夫提起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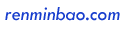



















 打印機版
打印機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