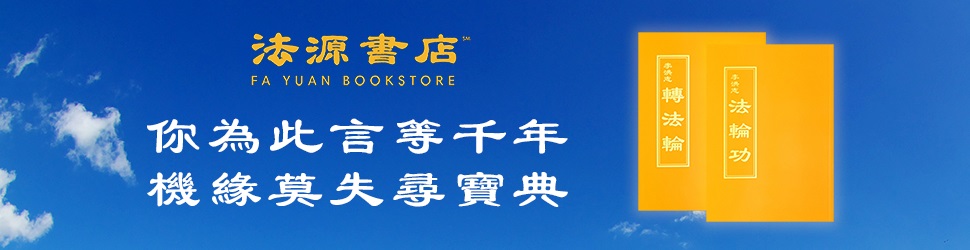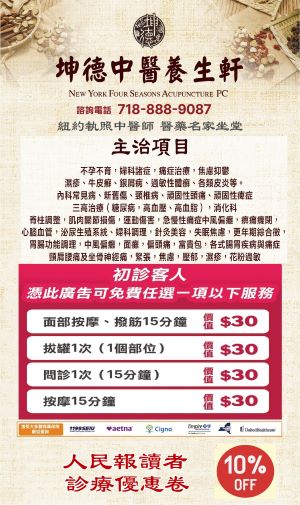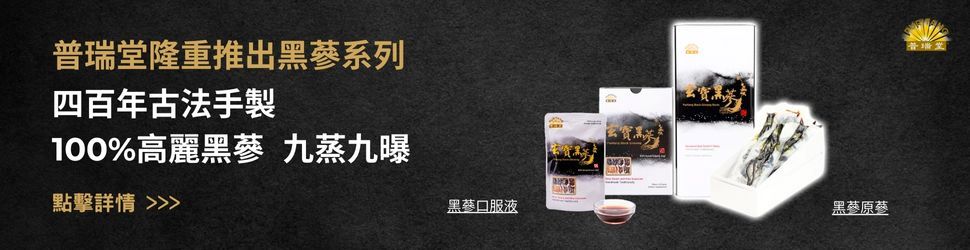習近平發表《憶大山》的雜誌截圖。
習近平發表《憶大山》的雜誌截圖。習近平在《憶大山》一文中,全面評價了賈大山此後幾年的工作:「上任伊始,他就下基層、訪羣衆、查問題、定製度,幾個月下來,便把原來比較混亂的文化系統整治得井井有條。在任期間,大山爲正定文化事業的發展和古文物的研究、保護、維修、發掘、搶救,竭盡了自己的全力。常山影劇院、新華書店、電影院等文化設施的興建和修復,隆興寺大悲閣、天寧寺凌霄塔、開元寺鐘樓、臨濟寺澄靈塔、廣惠寺華塔、縣文廟大成殿的修復,無不浸透着他辛勞奔走的汗水。」 士爲知己者死。大山是一個文化人,卻又是一個血性漢子。 在這裏,且講述幾個細節。 常山影劇院,被稱爲正定的「人民大會堂」,縣裏重大會議都在此舉行。但這座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的木結構建築,已成危房。近平提議重新建造。爲了保證質量,爲了保證工期,大山毅然決然地把鋪蓋搬到工地,日夜監工,雖然他的家就在千米之內。 正定隆興寺是聞名世界的宋代大型寺院,更是一處國寶級文物。但由於年代久遠,破破爛爛。若要全面修復,需要資金3000萬。如此巨大的投資,是當時全國文物系統除了布達拉宮項目之外的第二大工程。爲此,近平頻頻出面邀請國內權威專家前來考察評估,而大山則奔走於京城、省城和縣城之間,往返數十趟,直累得心力交瘁,胃腸潰瘍。他蜷臥在吉普車後座上,牙關緊咬,冷汗直流。由於長期出差在外,藥罐只得帶在身邊,白天跑工作,晚上熬中藥。最後,終於得到上級部門大力支持,落實巨資。 這項浩大的工程,還需要徵地60畝,拆遷60戶。其中困難,可想而知。 經過千難萬難,隆興寺修復工程終於圓滿完成。 至此,隆興寺真正成爲正定最鮮亮的文化名片! 春節期間,是別人最歡樂、最放鬆的時候,卻正是他最緊張、最揪心的時刻。九處國保單位,全是磚木結構建築,最易着火。每逢此時,他晝夜巡視,廢寢忘食。別人勸他,他說:「祖宗的遺產,國家的寶物,我負責守護。出一點點問題,我就對不起正定,對不起縣委,對不起習書記啊!」…… 歷史已經證明,賈大山用自己的聰明才智,按照自己的理想,爲家鄉的文化事業盡到了最大力量。雖然極其苦累,但也極其快活,極其酣暢。 不啻說,賈大山是那個時期全中國最得意、最幸福的文人! …… 這期間,近平升任縣委書記,工作更忙了。但他仍然忙中偷閒,一如既往地和大山相約見面,夜聊。 春雨潤青,夏日潑墨,秋草搖黃,冬雪飛白。歲月如歌,他們共同享受着友誼的芬芳…… 1985年5月的一個午夜,大山已經休息。突然有人敲門,近平請他去一趟。 原來,近平要調走了,第二天早晨7時乘吉普車離開。白天交待工作,直忙到半夜,送走所有同事,才騰出時間約見老朋友。好在,這個時間,正是他們最暢快的時光。 關於這一次離別,大山後來從未提起。倒是在近平的筆下,有一段清楚的記載:「……那個晚上,我們相約相聚,進行了最後一次長談。臨分手時,倆人都流下了激動的淚水,依依別情,難以言狀。」 兩人分手時,正好又是凌晨三點。近平最後一次送他到縣委門口,四目相對,心底萬千話語,口中竟無一言。與往常不同的是,這一次,縣委大門敞開着。 採訪時,大山妻子告訴我,那天晚上,大山回來時,懷裏抱着兩尊唐三彩:一峰駱駝和一匹駿馬。他一言不發,倒頭便睡,直到第二天中午。起床後仍是呆呆地發愣。 妻子以爲他病了,催他吃藥。他搖搖頭,慢慢地說一句:「習書記調走了。」 49歲那一年,大山辭去局長,功成身退,迴歸文壇。 這個時候,整個文學評論界驚奇地發現,他的小說已經發生了脫胎換骨的蛻變。「夢莊紀事」和「古城人物」系列數十篇短篇小說,微妙而又精確地發掘出文化和人性的敏感共通之處,禪意濃濃,芳香四溢…… 大山已經完全醉心於文學。如果說早年的他曾有過文人孤傲的話,那麼後期的他,則十足是佛面佛心了,慈眉善目,與世無爭,笑看風雲,其樂融融。 這其中,有一個細節讓人驚歎:大山名聞遐邇,卻從無一本著作出版。那些年,文學市場清涼。雖然出版界和企業界不少朋友主動提出幫助,但他笑笑說,不要麻煩你們了,還是順其自然吧。 賈大山,肯定是當時全中國惟一沒有出版過任何圖書的著名作家! 他的書房裏,懸掛着兩句自題詩:小徑容我靜,大路任人忙。 近平在南方的工作越來越繁重了,但他沒有忘記正定,沒有忘記大山。每遇故人,都要捎來問候。每年春節,都要寄來賀卡。 但大山卻鮮有回應。他知道,他的年輕的朋友,肩上有着太多太多的擔負。除了滿心的祝願和祝福,他不忍心有任何打擾。 1995年底,大山不幸患染絕症,近平十分掛念。1996年5月,他聽說大山在北京治療,便特意委託同事前往探視。春節之前,近平借去北京開會之機,專門去醫院看望。近平後來寫道:「我坐在他的床頭,不時說上幾句安慰的話,儘管這種語言已顯得是那樣的蒼白和無力……爲了他能得以適度的平靜和休息,我只好起身與他揮淚告別。臨走,我告訴他,抽時間我一定再到正定去看他。」 近平沒有食言。僅僅十多天過後,1997年2月9日,正是大年初三,他專程趕到正定。在那個他們無數次晤談的小屋裏,兩人又見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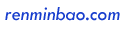



























































 打印機版
打印機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