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呵,呵。」我苦笑着,卻明顯有着許多無奈和苦衷。的確,在媒體工作久了,我們早就成了精神陽痿患者,成了表裏不一的陰陽人,成了一種畸形的混合體。這怪誰呢?曾經有一次,我在省政府門前採訪上訪羣衆時,羣衆嚷道:「看你們到底有沒有這個膽量報導這個事情?」
我沒有回答,但我知道,我沒有膽量。我寫出的稿子要經過主任、總編批,一些敏感的問題早就給槍斃了,哪能輪到我們記者自己作出決定?果然,還沒有等到主任審閱通過,報社就接到宣傳部的通知:「凡是涉及到上訪問題的稿件,一律不準報導。」
你看,面對這樣的媒體禁令,我們的同情心、我們的熱血還不是被擊得粉碎嗎?這樣的禁令使得現代媒體的真正宗旨變成了子虛烏有,也使得我們意識到中國新聞是沒有自由的。在媒體這麼多年,我接觸過許多禁令,有的以檔形式明確傳達給大家,比如領導講話、國家某種法令某種內幕、臺灣非國家、領導職務的排序等等都有嚴格的規定。一次,我們將市委主要領導的先後秩序排錯了,就招致了一場批評。還有一次,有一個記者採訪時將對方的「法輪功是一種信仰」的話寫了出來,就給了個黃牌……還有一些是宣傳部或者什麼主管機構通過口頭傳達下來的,比如本省的重大災難啊,惡性案件啊,貪官的腐敗行爲啊──就連最近因爲豬肉上漲、市場查處了許多病豬肉,也不讓報導,理由就是害怕人們引起恐慌,等等,都是禁令的範圍。
外省情況也大同小異。中國每一個省、市其實都是一樣:新聞是沒有自由的。廣州的一位報社的朋友這樣談道:
“辦公室門口有兩塊告示板,每週的選題清單、會議記錄、行政通知、版面安排等等都會貼在上面,除此之外,還要貼所有的禁令。廣州和北京是中國新聞界一南一北兩大聖地,精英多、水準高,這裏每天接到的禁令也特別多。多到什麼程度?每天編務的一項固定工作就是將這些禁令整理列印好,貼在告示板上,少時一天一張,多時一天能貼兩、三次,每次好幾張。我們辦公室門前的告示板因爲清理得比較快,到看不出什麼,18樓21室的告示板上,有時能攢好多天的禁令,那場面,很是壯觀。禁令一般有兩個級別,分別來自中宣部和省宣部,因爲南方集團是省級,所以廣州市宣管不着,照這麼推算,《廣州日報》每天收的禁令豈不是還要多上50%……”
以前在晨報的時候,每天也會有禁令。老總還會一本正經地在編前會上宣佈一下。部門主任回了辦公室還會強調一下。而在這裏,似乎完全沒人拿禁令當回事,其程度讓我覺得有點奇怪。禁令的內容比較五花八門,不過倒也沒超出以前在晨報的那些範圍:羣體性事件、重大案件、惡性事故、地方企業問題,等等。也有些禁令比較莫名其妙,比如前幾天有個老師爲救學生死了,按說是好事,但居然不準採訪。
另外一個特點是,可能是廣州的媒體太發達了,無孔不入,所以中國凡是發生點什麼值得一提的大事,不管是不是和廣州離着十萬八千里,幾乎都能夠在禁令裏出現。值得一提的是,這些禁令絕大多數並非中宣部發的,而是來自省宣。由此可以得出一個結論:能否和廣東省委宣傳部搞好關係,對一個地方的負面新聞曝光率會有決定性的影響。
聽北京來的同事說,那邊有人專門收集這些禁令,整理好了送出國去結集成冊出版。開始我挺奇怪,這種東西誰會感興趣。不過很快明白過來,原來,這種東西,才是對這個國家最真實的記錄。哦,還有另一種更真實的記錄,那就是新華社的《國內動態清樣》,絕密級,14億中國人裏每期能看到這玩意的應該不超過兩位數(問題是就這玩意也有收到禁令的時候)。
你看,在這種禁令的摧殘下,難怪記者們雖然思想上「反動」,而行動上卻日趨保守了。但新聞的不自由無疑是中國媒體從業人員的悲哀,因爲大家都快變成了瘋子,變成精神分裂症患者了。
---------------------------------------
新唐人電視臺首推「全世界華人聲樂大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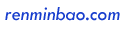


























































 打印機版
打印機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