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1921年成立以後,僅僅20多年就已星火燎原。這說明,共產黨在早期有強大的感召力。它在建國初期吸引一些海外學子拋棄優越的科研和生活環境回去報效祖國,在抗戰時期也曾經吸引無數青年投奔延安。然而,許多投身共產黨的人沒有死在敵人的手裏,卻死在共產黨的槍口下,沒有進過敵人的監獄,卻幾次關進共產黨的牢房。反右和文化大革命更對千百萬家庭造成極端痛苦的傷害。一次次的浩劫以及開放之後瀰漫全國的腐敗之風,使許多人改變了對共產黨的看法和感情。
新中國的成立激勵着芝加哥大學的英國文學博士巫寧坤,促使他在1951年不顧朋友的勸阻回到北京報效祖國,在當時的燕京大學英語系擔任教授。他說:「系主任趙蘿蕤博士是我在芝加哥大學的同學,她邀請我回去。我是一直想要回去的,從來沒有想要呆下去。現在聽到祖國的情況,新中國嘛,國內親友來信都讚不絕口。所以我就想回去,爲新中國的建設盡我的一份力量。」
然而,在美國想說什麼就說什麼的習慣使巫寧坤每次運動都捱整。他詼諧地說,他剛剛回國,就在當年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中當上了「運動員」。他說,有些人把他平時說的話悄悄記在小本子上,令他吃驚。「最使我吃驚的是,怎麼會有那麼多人監視我,我帶的寫論文的學生都把我彙報上去了。這是很驚人的,對我思想打擊很大。」這樣,在1952年的院系調整中,巫寧坤被送到了南開大學。
1955年肅反時,他被打成南開頭號反革命,全家被抄家和搜身。1957年共產黨整風,號召「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巫寧坤提出言論自由等問題,結果被打成右派骨幹。他先在北京短期關押了一陣子,女兒在這個時候出生,他都不能看上一眼,就被送去北大荒勞改了:「而且在這個期間,我的女兒出世,我也見不着。我太太讓我起個名字。我給女兒起名『一毛』,幾天以後我就去北大荒了。」
巫寧坤在他後來寫的書《滄海一淚》中回憶到,在勞改期間正值所謂自然災害時期。有一天,他被看守派去挖土坑,挖好之後,一輛馬車拉來了破席子卷着的一具屍體,他打開席子一看,原來是他認識的老劉。他想,「連老劉這麼健壯的人都餓死了,怎麼知道下一個不是我呢?」
文革期間,巫寧坤自然也躲不過挨鬥和進牛棚的命運。1979年巫寧坤被落實政策回到北京。然而,蹉跎歲月已經無情地浪費他20多年的寶貴時光:「22年,也就是我們有用的歲月,就這麼荒廢了。」這些荒廢的歲月粉碎了他的夢,成爲他最大的遺憾:「我想當學者,這個夢沒有實現,想當作家也沒有當成,反而讓家人受罪。 」在中國經過幾十年的磨難之後,巫寧坤如今又回到美國定居。這種歸宿看來就是他對自己當年回國的決定做出的反思和結論。
早年參加革命的女幹部戈揚在三十年代就仰慕共產黨,嚮往解放區。於是,戈揚在1941年參加了新四軍。她回憶說,當時的共產黨是有理想、有正義的:「那個時候的共產黨是有理想的,當然是不合實際的理想,例如『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殺了夏明漢,自有後來人。』當時的共產黨是有正義的,要求抗日也是愛國的。我們青年就在這樣一股熱潮中參加了共產黨。」
然而,戈揚說,解放後不久她就莫名其妙地被打成了右派。但是,也正是當右派後的種種磨難使她改變了對共產黨的認識:「就是打成右派以後被送到農村去受苦,才認識到一點真理,轉變思想。」文革以後戈揚在復刊的《新觀察》雜誌擔任主編,但是她已經不再仰慕共產黨:「我當然討厭它,很討厭它。我還沒有發現共產黨對人民做過什麼好事。」
著名的《上海生與死》一書的作者鄭念,在她的這本書裏詳細記載了她的遭遇。鄭念爲殼牌石油公司在上海的辦事處工作,文革弄得她家破人亡,她的女兒因爲不肯說自己的母親是特務被活活打死,然後屍體被人從九層樓的窗戶扔下去,以造成自殺的假象。鄭念本人被關進監獄,單獨囚禁了六年半,受盡折磨:「打我,當然了,一天到晚打我。給我上背銬,上了11天。我到現在還有疤。我出獄時體重只有84磅,我正常體重是115磅。」
鄭念在文革結束以後來到美國定居,她說,只要共產黨在臺上,她絕不回國:「我一輩子不回國,除非共產黨倒臺。共產黨只要還在臺上,不管是保守派也好,改革派也好,我絕不回國。」不過,鄭念也承認,共產黨也做過好事,這件好事就是解放了婦女。
黑龍江省一名四十歲的兒童醫務保健工作者給美國之音打來電話說,他小時候非常敬仰共產黨;「小時候我敬仰共產黨,也敬仰革命先烈。那時候沒有吃不上飯的時候,三年自然災害過去之後,家家都能吃飽。」他說,在林彪走紅的時候,他對共產黨的感情淡了下來,到了鄧小平時期就更淡了,許多工人下崗,他也下了崗,全家人均生活費只有一百多元,遠遠低於國家的人均300 元生活保障線。
這名下崗人員說,「六四事件」以後,他對共產黨就徹底絕望了:「在江澤民當政時代,尤其是六四以後,我對共產黨一點感情也沒有了。我也有親人、熟人死在天安門廣場,甚至就是因爲去天安門喊聲冤而被抓並打死。我對共產黨徹底絕望了。」
摘自(新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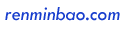

















 打印機版
打印機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