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中央美術學院畢業,畢業以後就被捕,當時只不過沒有拉出去槍斃而已。我是被作爲死刑犯處理的,我在看守所裏等於是「死緩」,被關了六年,以後正式改判爲十五年徒刑,去服刑。打倒「四人幫」以後平反出獄,前後在監獄裏被囚禁十年。
出來以後,我又回到中央美術學院教書。教了兩年書之後,因爲我太太家在香港,八零年初我到了香港,在香港居住八年。一九八九年到了美國,先後在普林斯頓、康乃爾大學、德國海德堡大學,在大學訪問或任教差不多十年。
現在,我自己決定回到中國,想要了解國內人的想法,倒不是因爲使命感,而是覺得我自己內心的很多東西沒有完成。我在海外總有一種隔靴搔癢的感覺,所以也就不避海外一些朋友說我是向當權的屈膝投降,回來了。其實這是不存在的問題,因爲我自己覺得應該做的事情在這邊。我做的都是人文方面的,就是寫一些東西,想弄清楚大家心裏真正的想法。對於過去的一些東西,我們民族沒想清楚,我自己也沒想清楚,現在又被什麼東西遮蓋着,所以,我現在做的就是弄清這些。
我當時坐牢的罪名,是因爲當時在北京學生中間,尤其是在文藝界的學生中間,傳起了關於三八年黨中央不批准江青和毛澤東結婚的事。實際上,是因爲文藝界對江青知根知底,關於文革,現在說都是「四人幫」的罪行,其實原因更復雜,大家的怨氣都直對着江青,是因爲她迫害文藝界的人比較直接。
當時,江青就搞了專案組,想要知道是誰把這些消息傳出來的,這些資料從哪裏來的。專案組成立後就開始抓與這些言論有關係的人,我們就是在這種叫作「清理階級隊伍」的過程中被抓的。那時中央美院只有一百多名學生在校,就抓了差不多三、四十個學生,不是正式的逮捕,而是像有些中學一樣,設立了「地下黑監獄」審查這些人;此外,又抓了幾十位老師,都是用嚴刑拷打,然後讓每一個人說出,你聽見這些話是誰說的。同樣,在音樂學院等所有的藝術院校和文化部下屬單位,都在做同樣的事;經過篩選之後,慢慢就弄清楚哪些人是「主犯」。
開始抓人是在六八年一月份,到五、六月份就基本上理清了哪些人構成「反革命集團」、哪些人屬於更嚴重的「集團」。我就屬於這個最嚴重的「集團」。我是一個主犯,當時用的詞是「被扭送公安局」。實際上,北京市公安局從一開始就介入了審判,因爲真正抓到公安局,如果打了你,將來案子沒有成立,你出來還可以告他,所以在公安局授權和監視之下,讓你的同學打你。這些刑訊手段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無論你有多麼堅強,都不可能不把所有的話講出來,因爲當時根本就沒有什麼攻守同盟,這些人是突然之間被抓起來的,大家事先都不知道怎麼回事。接着是挨個被打,問他們說過什麼話。我估計一共逮捕了有六、七百人吧。我所認識的文藝界被捲進這個案子的人有幾十個,比較有名的,像後來當了文化部副部長的英若誠,中央樂團的副團長,也是首席小提琴的楊秉孫,都是在這次風潮中被捕的。後來要給這些人判罪,而且要有威懾力,就要給他們釐定更多的罪名。在這些手法上,和給遇羅克定罪的過程都是異曲同工,你真的做了什麼,同最後給你定的罪名,沒什麼關係,不過是一種說辭。
我最後被判刑的罪名有三條:第一條,他倒是說對了,是所謂「惡毒攻擊中央首長」,就是講了江青最不愛聽的話,還講了當時領袖的笑話,還有對當時中央首長的行爲做過評論、批評,都算是罪行。在最緊張的時候,只要說過中央首長一兩條壞話,有人證明,那就會被判死刑。當時,給我弄了一百多條這樣的罪行,當然是槍斃幾次都不嫌多了。第二條罪行是和後來判魏京生的說法一樣的,就是「裏通外國」,因爲我認識一些法國留學生,跟他們聊過天,就算是「裏通」法國。還有第三條,就是我們曾經商量過出國留學,因爲我是學西方藝術史的,想去法國留學,這犯了「陰謀叛國投敵」罪。我就是按照這三個罪名被判處死刑的,案情就是這樣。
我跟遇羅克第一次見面是在一九六八年,大概是十一月左右。我們在北京市看守所,那裏關了很多學生。因爲釋放了一批聯動分子,原來跟我關在一起的人都被放了,把沒有放出去的重新編號,重新組合。在這次組合時,把我分到新地方。北京看守所有三個樓,像一個K字,叫做K字樓,是三層,我們被關在K字樓的二層,叫六筒,我大概是在六筒一號,號子裏已經有人住過一段時間了,遇羅克就在這裏,我們一直到一九六九年跟他在一個牢房裏,被管了差不多半年。
到了一九七零年四月九日,我被調到死刑號裏的時候,我和遇羅克又都是在死刑號,我在四筒,他在二筒(還是三筒?)。那時,都是單間,我們只是在晚上,看守不注意的時候,才能說一兩句話。有時聽他跟看守說話,只是間接地知道對方跟自己一樣,是死刑犯。我跟遇羅克的接觸主要是那半年關在一起的時候。
每個房間大概就是十多平米,關了二十個犯人,當時政治犯太多了,牢房裏的擁擠程度是,如果每一個人都躺平了的話,就躺不下。睡覺時只能側着身子,如果誰想翻身,要大家一起翻。晚上起來解手,再回去就要把兩邊的人拼命地推,才能擠進去。
北京看守所爲了管理方便,在三個建築羣中間都有一個廳,值班的警察和看守都在廳裏,而伸出來的每一個走廊就叫「筒」。英文的「K」字有三個筆劃,從中間看,一層就是一、二、三筒,二樓就是四、五、六筒,三層是七、八、九筒,四層是十、十一、十二。我們當時就在二層的六筒一號,後來又調到七筒。
我一進入六筒一號,碰到遇羅克的時候,實際上在別人向我介紹說,那是遇羅克的時候,我馬上就知道他是誰,我在監獄外面就知道他的大名,也讀過他的文章。
當時抓我的罪名之一是說我是聯動的後臺,或者說是聯動的思想後臺。第一次抓我的時候,公安局自己不出面,而讓美院附中的「四三派」把我抓起來,「四三派」是同所謂「老兵」(老紅衛兵),也就是後來大家說的「聯動」,對立的,因爲我跟幹部子弟出身的人有千絲萬縷的關係,於是當時海淀區最能打架的石油學院附中的「老兵」,就派了很多人來,和別的很多學校來攻打美院附中,來搶我。
結果,引起武鬥,雙方打得激烈的時候,就在早上四點鐘左右,我逃走了,一直逃到石油學院附中。爲了安全,我和當時聯動裏最能打架的人住在一起,也跟他們談文化,談理論,後來石油學院附中被包圍,我又跑了,他們被打得也夠慘的。聯動裏面最能打架的人叫賀邯生,他被打得不能生育,絕了後。當時,「四三派」的理論基礎是遇羅克的《出身論》。我因爲跟聯動在一起,從表面上看,我是個血統論者,但是實際情況比人們想象的要複雜得多。
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我們是少數派,當時被整得也很慘。後來,聯動被抓,我又跟聯動在一起。平心靜氣地說,同樣因爲言論罪被判死刑,遇羅克和很多人都被槍斃了,而我們最終沒有被槍斃,還是因爲出身好而佔了便宜。
所以,我一開始聽說他是遇羅克,對他就有一個誤會,因爲他肯定會知道我的背景。不知道當局是有意還是無意,把有聯動背景的人,和一個與聯動有仇恨的人關在一起。當時,我的朋友是像彭小蒙那樣的人,是紅衛兵裏的「筆桿子」,還有像魏京生,當時也是聯動裏搞宣傳的,這都是我的鐵哥們,而遇羅克的朋友是牟志京,所以在社會上,兩派人是極端對立的。但是,可笑的是,我們都被關了進來。說實在的,當時聯動分子在獄中的待遇比他們要好得多。而且,當時聯動的人最後都被放出去了。我仍被關在裏面,主要不是因爲我是聯動,而是因爲江青的事。
遇羅克一開始不知道我是誰,表現得很主動。我就是一個學生的樣子,那時候才二十四歲,自己認爲很成熟,實際上很幼稚。大家當時都是愁眉苦臉,遇羅克卻是笑眯脒的。他走過來,對我說:「我姓遇,愚公移山的愚字,去掉下面的心字,再加個走之,羅霄山脈(井岡山根據地之所在)的羅,克服困難的克」。他就是用這樣開玩笑的、幽默的態度介紹自己。我就說:「久聞大名,我讀過你的文章,我覺得你的文章寫得不錯」。我對遇羅克說的是真的,因爲他的文章邏輯清楚,論點明確,而且是說中了要害。遇羅克覺得很奇怪,一問我的名字,他更感到奇怪:「你還讀過我的文章?」——後來,遇羅克說過,他當時只是寫文章,比如他寫《聯動的騷亂到底說明了什麼》等等,他只是在文章上與這些人交鋒,他希望有一個公平的機會,就像古代比武,拋開社會所附加的不合理條件,大家公平地較量一番。他當時對我們也有一種好奇心,像我對他有好奇心一樣,因爲我們生活的社會層面完全不同,都想知道對方是怎麼想的。
所以,一開始我們都是帶有戒備心。想想很有意思,我們的談話有點像外交辭令,談什麼問題都不像是普通的聊天,而且有點不約而同。牢房裏也有殺人犯、武鬥打死人的人,也有過去的中統特務,也有革命老幹部。遇羅克雖然不是大學生,但是他的學識比別人高很多。那時,監牢裏所有的人都知道,來了我這麼個大學生,中國人當時比較認這個頭銜,所以大家就讓我給他們講故事。但是,我有一個感覺,遇羅克的知識面不比我窄。當我講故事的時候他不會聽,只是看他的書,或者去睡覺。因爲我的常識性講解對他說來沒有什麼意思。
等到大家累了休息的時候,我和遇羅克都會主動坐在一起開始談話。因爲,知識的背景和結構不一樣,而且在文革中的處境也不一樣,所以談到一些問題的時候,他就會說,「據我的經驗,據我的學識,這個問題不是這樣的」。但是,我那個時候也是少年氣盛,他說完以後,我也會同樣說,據我的經歷,據我的學識,事情就是這樣。開始時,總有這樣的爭拗。後來,不可避免地談到了血統論問題,這是冰釋我們之間誤解的開始。
有一天,他跟我談起電影,他先問我,你看過《馬門教授》那個電影嗎?那是東德拍的電影,主題是反法西斯的,中間有一大部份描繪馬門教授,他是一個猶太醫生,當時,猶太人在德國柏林受到迫害,學校裏也對猶太學生迫害。他一說,我就知道他要說什麼。
我說:「看過」。我又說:「跟中國沒有什麼區別」。
他說:「你會這麼看嗎?」
我說:「我覺得是這樣。我在看的時候還不知道,但是到了文化革命,就發現,出身不好的人的處境,跟猶太人沒有什麼區別」。
遇羅克說:「你們也會這麼看?」他又問我:「那你看過《出身論嗎?」
我說:「《出身論》寫得不錯。但是,有的時候人們會得出一個結論,就是出身越不好的人,就越革命……」。
他就談到,《出身論》當時也是一種宣傳,因爲要宣傳自己的觀點。
經過這一次,大家談出自己觀點的要點,我們就把這個話題放下了,因爲它已經不是一個針鋒相對的焦點了。所以,我們就能夠比較放鬆地交談。他跟我談了很多他的童年時代,他們家的大院,他和弟弟妹妹的關係。談及他在學校功課好,因爲出身不好沒能進入大學,而被排除在「遊戲」之外。
在這個過程中,我發現我們的經歷確實很不一樣,我是在所謂的好學校一直升上來的,我才知道這個社會對大家是不公平的,在和遇羅克交談之前,我對這個社會了解並不多。而在這一方面,遇羅克比我清楚得多。他跟我講,他在農場種草莓,在街道上怎麼跟人搞好關係,怎樣傳呼電話……他在社會上交往的能力比我們強得多。至少,他使我了解了社會的另一面。
最難忘的事情就是我們在一塊兒編詩集,我們把手紙裁成像豆腐塊那麼大,然後他想辦法弄到紙和筆,假裝寫材料,實際上寫我們自己背的詩。把過去學過、讀過的古詩,一首一首地記錄下來。可以想象,監獄生活是相當枯燥的,是度日如年,但是,遇羅克一直在學習,我對他比較佩服。我當時對於自己會被判這麼重的刑,始終耿耿於懷,大惑不解,而且一口氣難平,覺得是被別人迫害,完全是個人恩怨的一種陰謀,所以,我在監獄裏給大家講《基督山恩仇記》,遇羅克也在場。
這時候,能和遇羅克一塊編古典詩詞,大家都覺得生活中還有文化,還有些情趣,在談詩論詞的過程中,暫時忘掉鐵窗中的殘酷。因爲,我周圍的人經常是這個被打、那個被戴上手銬腳鐐,天天見到的就是鐵和血,還要假裝視而不見。
當時給我印象比較深的是,每個牢房裏都有幾個被折磨的神經失常的人,他們也是遭遇最慘的人。有一個是當時的「北航」,現在叫「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的老師,教俄語的,我們叫他王老師,他已經變得半精神病了,誰都可以在他身上踢兩腳、打幾拳;另外一個是個農民,因爲說他罵了毛澤東就被關進來了,進來的時候,戴大鐐銬,人已經被折磨得變了形,大家打他打得更狠。
那時候,我作爲一個學生,從來不動手打人,我的良心也受不了這樣的事。當時,我們就跟值日似的,輪流管精神失常的人,因爲他們自己連上廁所都不行,得有人拽着走。輪到那些小年輕管他們的時候,就要表現一下自己的心狠手辣。等輪到我的時候,他們說,讓這個「聯動」來管他,聯動打死人都不眨眼,意思是我能把他們打個半死。當時,我沒有必要向他們解釋,我也不想像別人那麼做,別人覺得我假慈悲。
當時遇羅克對他們的態度很特別,也不打他們,但是也不對他們好,完全不把他們當成一回事,就是視而不見。當時,我很奇怪,問過他,我說,那個俄語老師畢竟是老師啊。遇羅克的意思是,他們已經精神失常了,你對他好與不好對他們都沒有用。他還說,在社會上值得同情的人多了。
我想,可能他在社會上時間長了,總是同情人就會被認爲是「爛好人」,是沒有用的。從這一點上,我想遇羅克遇到的事情中有比這殘酷得多的,所以他不會婆婆媽媽。我想是不是他更理智,更接近一個政治領袖?
中國那個時候如果有民主選舉的話,他會得到很多人的選票。因爲,在我們的牢房中這很明顯。我們牢房有很多殺人不眨眼的人,但是對遇羅克都畢恭畢敬。他們對我倒沒有,量我不過是一個學生,仗着政府對我們好一點就胡作非爲而已。但是,遇羅克不一樣,因爲誰都知道他敢跟政府較勁,在牢房中就是真正的英雄。而且,他又是《出身論》的作者,是當時在中國被污辱被損害的最底層人的代言人,所以這些人對他非常尊敬。
有時,我跟遇羅克爭論得很厲害的時候,這些人都在旁邊摩拳擦掌,意思是我要有什麼不軌的話,他們就會一哄而上。但是,我們沒有那樣的問題,只是理論和觀念上的衝突。
在另一方面,遇羅克也有他特別孩子氣的一面。他也願意跟我們一塊唱歌,也跟我們學了一些歌,還和我們一塊下圍棋、下像棋。他下像棋可以下盲棋,我們根本下不過他。
想想那時《中學文革報》影響那麼大,有多少人寄錢,或要求幫忙,有人想見他都沒有機會。當局把他們打成反革命集團,就是要打擊他,這一點他很清楚。我說,你這樣做後果很嚴重。他說:「你們出夠了風頭,而我們的聲音沒有人能聽得見,每個人都是先天性的軟骨病,沒辦法。現在,好不容易有了機會(他指的是,當時中央文革一會兒支持這一派、一會兒支持那一派,他們從中有了辦報紙的空間)」。他們找到這個機會,發出了最強音,比我想象的還要強,所以他說,爲了這他很滿足,就爲這個,不管付出什麼代價都值得。
實際上,至少在我跟他同監的時候,他認爲可能是長期監禁,他沒有想到會判處死刑。爲什麼呢?當時我們談過這個問題。中國當時雖然有很多反革命罪犯,但是他們都是有具體的罪行,從這一點來說,我會比他判得重,因爲我有裏通外國等罪名,而他連這種罪名都沒有,他只是因爲一篇文章,而且,他知道陳毅對於出身問題的看法跟他一樣,他也通過途徑跟陳毅聯繫過。因此,遇羅克當時跟我說,他對我很理解,也很同情我的處境,他知道我肯定會被判死刑,但是執行不執行還不知道。他曾經對我說,如果我有機會先出去,一定會替你陳情,去找陳毅,想辦法爲你斡旋,使你免於死刑。我還很高興,對他表示感謝。我當時已經到了只想求不死的程度。那個時候遇羅克並不知道他會被判死刑,那個時候他的案子還沒有判決。實際上,我們都沒有料到一九七零年「一打三反」開了這個殺戒,以思想罪正式槍斃人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我們在一起的時候是一九六八年,還沒有估計到後來會有「死刑,立即執行」這樣的結果。
後來,我們在死刑號的時候我很佩服他,因爲按照中國的程序,進了死刑號就是一定要被槍斃的。等我們都進了死刑號的時候,當時我被震驚了,所有的人都被震驚了,我們都處於一種頭腦空白狀況,我不知道心理學上如何解釋,當時不是害怕,也不是失常,而是一種愕然,就是人怎麼樣來面對這樣的現實,面對你將要被處決。
在這一點上,遇羅克比我們強。他在的死刑號裏向管理員大聲「報告」,實際上是說給我們聽,他說:「上一批的幾十個人都去見馬克思了,只剩下我一個人了,因爲我有重大案情要細細交待,可沒什麼人提訊我,我怎麼交待啊?」,讓我們有個思想準備。那時候,他的語調還是那麼平靜,一聽就知道,他是帶着微笑說的。這時候我就比較佩服他,他的心理素質要比我們強得多。
當時跟我們一塊進來的社會科學院(當時叫學部)的一個「筆桿子」叫沈元,他一進來的時候,就愕然了。我們被拉出去批鬥,戴上十幾斤重的鐵鐐,身上插着生死牌,在兩場批鬥中間休息,吃乾糧的時候,沈元還跟我說,聽說是「批鬥從嚴,處理從寬」,我一聽就笑了,我說沈元你還那麼天真,你沒聽見遇羅克說的嗎?你應該做更壞的準備。沈元說,怎麼會呢?我說,可能我們都得被槍斃,沈元說,有那麼便宜嗎?我說,你說不便宜是什麼?難道是終身苦役?還不如死了。
其實我話是這麼說,人還是希望活着,等我們到又一輪批鬥時,看到前一輪挨批斗的人都被槍斃了,沈元回來後,就受不了了,也可能是他想要延緩這一過程,就隍7d始裝瘋,喊、哭、叫。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處理方式,我就有些不明白,人在裝瘋時會不會真的瘋了?
遇羅克一直在拍打專門安在死刑號裏的按鈕,只要按了,隊長就會來。遇羅克故意找茬兒跟他們說話,把想要跟我們說的話跟他說,讓我們聽。遇羅克始終保持這種狀況,一直到三月五號他被拉走槍斃,他的情緒一直非常穩定,這一點是我所佩服的。
我沒有像沈元那樣裝瘋。裝瘋不止他一個人,我們也弄不清究竟誰是真瘋了,還是裝的,反正後來都被槍斃了,也沒辦法考證了。我和其他幾個人就是沉默,並沒有像遇羅克那樣繼續向他們挑戰,我覺得,做任何事情都是沒有意義的。
從六八年十一月到六九年五月,遇羅克一直和當局在審訊上進行較量,一直到進入死刑號,他還是那樣,這是遇羅克跟我們不一樣的地方。這說明,每個人的心理素質,以及他對於生活的選擇不一樣,表現的就不一樣。所以,我覺得遇羅克在那個時代,只能作爲一個犧牲的英雄,他的選擇一定是這樣的後果。因爲我後來知道,審訊他的審判員姓丁,因爲個子很高,都叫他「丁大個兒」,丁大個兒對遇羅克恨之入骨,但是,直到六九年的時候還是定不了遇羅克的罪。丁大個兒就說,好,定不了罪更好,就等機會。一直等到七零年「一打三反」,他真正如願以償,把遇羅克送進死刑號。
當時時代一定會「成全」像遇羅克這樣的有自己信念的人。這個政權、這個專政機器是會「成全」他,這是雙方的成全。這個專政機器是靠人的鮮血奠基了它的「合法性」。我們爲什麼沒有被選擇犧牲,是因爲當時我們的血統,這是社會上不成文的因素。另外一方面的原因是,我們還不是當局槍殺的最佳選擇。從這個角度說,現在很多人要紀念遇羅克,我覺得這個意義是很長遠的,但是,也有它的侷限。
從長遠的方面說,我們不能忘記歷史,就像德國人一樣,還要看《辛德勒的名單》,德國人還要知道納粹爲什麼能夠在這麼優秀的民族產生。中國完全不一樣,中國現在好像在物質文明方面大大提高了,整個社會比原來開放了,有了民間的口頭言論自由,但是在思想的箝制和言論的限制上沒有比當年進步多少。所以,我覺得這本書《遇羅克遺作與回憶》有它的侷限性,它沒有辦法,在這樣的環境下,只能出版這樣一本書。問題的焦點不在於那個時代錯殺了一個民族英雄,而在於,中國有沒有一天可以讓大家有真正的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如果沒有思想和言論的自由,物質再豐富,中國還是一個原始的、落後的、嚴酷的社會。這一點沒有什麼改變。
在八零年遇羅克得到公開平反之前,我已經知道了。因爲當時遇羅錦通過別的途徑找到我,接着是一些報社的記者跑來找我,因爲我是唯一跟遇羅克在最後的時刻、在死刑號還在一起、並且願意說出來的人。實際上不止我一個人有這個經歷。當然,有的人已經死了,也有的人不願意說了。
那個時候,我一聽到這個消息,就有一個錯覺,認爲中國進步了。因爲八零年初的時候,雖然政府把「民主牆」從西單搬到月壇,但是整個的感覺是中國有一個可能性,街頭大字報不行,可是在私下的思想自由已經開始了。遇羅克這件事情真正的平反對中國說來是一件大事。
我當時馬上給香港的《九十年代》寫了一篇紀念遇羅克的文章。一開始,他們沒敢發表,後來發了,就是現在《遇羅克遺作與回憶》中收入的那一篇,遇羅錦也借用了我的一些資料。當時中國如果開始反省這些問題的話,我認爲這個民族很有希望,我以爲這是一個理性的、往前走的過程,但是,魏京生的事情又出來了,於是就變成遇羅克平反、魏京生被抓。
中國歷史很有諷刺性。魏京生本來是聯動裏搞宣傳的,他變成了向極權挑戰的人;而當時出身不好的遇羅克,發表了《出身論》的人,跟張志新一樣,被政府當作一個民族英雄的形像來宣傳。這件事有它讓人激動的一面,也有讓人沉思的一面。那時宣傳遇羅克是真的想徹底反省這件事,還是僅僅是一種需要?實際上後來我發現,對於遇羅克的宣傳時間很短,沒有深入地討論,因爲如果深入地討論,進一步談「一打三反」運動的過程,就會談到那時殺了多少因爲言論、因爲思想獲罪的知識分子,大部份經過正式宣判,還有一些在沒有宣判之前就被打死在地下室了。
這些人和第一波紅色恐怖時被打死的人不一樣。紅色恐怖中打死的差不多都是出身不好的人;第二波打死的人是造反派武鬥,死的是羣衆;在清理階級隊伍以後殺死的人,都是政權所不喜歡的人,是以羣衆運動的名義殺死的有思想的人。我想,只有把這些事情談透之後,中國人才會知道思想自由對於中國的社會意義,這個民族才會有希望。一九八零年,遇羅克的事情才說了幾天,就不再提了。根本就沒有人把「一打三反」,這個箝制言論、扼殺思想的頂峰拿出來批判。好在「一打三反」沒有延續得太長。否則,不知要殺死多少人!
談到這本書《遇羅克遺作與回憶》的不足,我認爲,如果真的從理論上來談遇羅克這件事,這本書出版就會很困難。所以,它還停留在打倒「四人幫」啊、「四人幫」製造的事端啊,這些提法上。當然,事實遠遠不是這樣。我曾經想過,要從現在的角度重新寫遇羅克,但是,讓人感到悲涼的是,像《九十年代》這樣的知識分子的言論刊物都被迫停刊了,那我寫這樣的文章能在哪發表,誰還會去看?我拿着這本書給現在的年輕人看,他們翻了翻,第一個反應是,那時候你們怎麼那麼傻?意思是,那麼錯的事,你們都站出來說話不就成了嗎?我就只能說,那時候站出來說話的人都死了,或者被打壞了;他們的第二個問題是,那是真的嗎?他們根本不能理解,而且以爲他們現在已經享受到最充份的思想自由、言論自由了。但是,這些你不能跟他們辯論。
我覺得紀念遇羅克應該從更深層來說,救救這個民族!救救這些孩子!我們應該更深入地來討論這些問題,從文化上弄明白,現在我們的毛病在哪裏。
我不是唯一活着從死牢裏出來的人。跟我一塊兒出來的還有一個姓周的,他和我是同一個案子。但是,每個人的選擇不一樣,他不但不願意再提這件事,也不許別人提他的名字和他的事情。他覺得這個回憶對每個人來說都非常痛苦,誰要是提起,就是用人們的痛苦來賺自己的錢,或者賺自己的名聲。也有別人對我提出過這樣的批評,不光他一個人這樣說。但是,我這些年來寫的都是這些,已經快要變成「監獄文學家」了。其實靠這個既發不了財,也出不了名。
我覺得,我應該講一個故事。就是在第一天,二月九號我進到死刑號,遇羅克大聲和看守說話,暗示我們真相以後,當時每個人都被震驚了,那個時候走廊裏面靜得連一根針掉到地上都能聽得見。每個人都處在臨死前,進入了死亡的程序中。我們聽見獄卒進了房間,那是二月初北京的冬天,剛下完雪,他把牢房門關上了。我們都輕輕地提着腳鐐和手銬站起來,每個人都貼在自己的那個小窗戶上,互相開始叫名字。這時候,我就想起日本小說《喬遷喜面》,寫的是,本來人們爲了慶祝喬遷之喜要吃一頓面;共產黨員在監獄裏轉監的時候,會開一個晚會;我就提議,咱們做一個臨別的晚會吧,大家都同意,然後我們就輪流唱歌,當然是以很小的聲音。但是,牢房太靜了,只要一個人唱就都能聽見。我突然憋不住了,就大聲唱了起來。這時候,看守就衝了出來,大叫「誰?」我們趕緊躺下了。他過來查,我們都假裝睡着。後來就變成這個晚會很滑稽,他跑回去,我們就躺在床上大聲唱,他出來就不唱。我唱的是曾經跟遇羅克一起唱過的歌,包括《光榮犧牲》這首歌。
我可以說,遇羅克是比我更正統的理想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所以,他的哲學的整個框架是黑格爾、費爾巴哈到馬克思主義。但是,他反對馬克思之後的國家與政權這一套,他是非常理想主義的。
他想起這些歌的時候與當時的處境有關,那時他戴着很緊的手銬,吃完飯,手就會腫脹,非常難受。那天吃完晚飯,他就跟我談起來。那時大家都知道這樣一個傳說,斯大林最喜歡的歌是《蘇里柯》,格魯吉亞民歌;列寧最喜歡的歌是《光榮犧牲》。我因爲過去一直學外文,喜歡唱外國歌,俄羅斯歌差不多都會。遇羅克問我會不會唱列寧喜歡的《光榮犧牲》,我說,會。這是一首根據俄羅斯民歌改編的歌曲,我們就一遍一遍地唱,唱得監獄中的老頭都哭起來了,因爲處在那樣一種環境,大家都有一種帶入感。
在死刑號裏的第一夜,大家都沒有睡覺。我還記得,有一個小孩,忘記他叫什麼了,可能是因爲偷越國境到當時的北朝鮮,被北朝鮮當局送回來了。看他歲數小,我對他說,你出去的機會最多,你出去以後一定要告訴我爸爸媽媽,說最後我們沒有難過,最後我們挺開心的,還一直在唱歌。其實,當時我自己覺得沒有什麼可求的了,希望外面的人不要爲我們難過。我也跟前面提到的那位姓周的說,看來咱們活着出去的機會不多了,咱們以後到上面去,跟上帝一塊兒的時候,互相讓着點。遇羅克也跟我們搭茬兒,他好像說「殊途同歸」之類,具體我記不清了。大家一起唱歌的時候,遇羅克也唱了。
現在我知道的,還有兩個人沒有被槍斃。他們曾經到北京看過我,大家記得最清楚的是這次獄中晚會。但是,他們因爲有各種考慮,不願意談這些事。
遇羅克個子比我高一點,大概一米七二左右。我一進監獄的時候,是十一月,監獄裏還沒有生火,很冷。他戴着一頂栽絨的棉帽,就像解放軍戴的那種。監獄裏的老工人叫他冬瓜腦袋,因爲他的頭有點平行四邊形,有些禿頂,戴着黃框的眼鏡。他說話嗓音有點尖,慢條斯理,寫字受魏碑體的影響,字很漂亮,我算是中央美院畢業的,但是鋼筆字不如他寫得好。
使我多年不能忘記他的地方是,他在任何環境都能夠保持一種寧靜的心態,因爲他有一個堅定的信仰,這是我始終沒有的,到現在我也沒有。他對我的影響可以說是他的使命感,這使命感比較明確,就是要爲這些出身不好的人鳴不平,爲這些人爭取應得的權利、地位,實際上他也是在爭言論自由。
我本來應該從監獄出來好好作生意、去發財,或者做一個閒散的人。但是每次只要有什麼事,比如「民主牆」、「六四」,我都不可避免地捲入其中。是遇羅克的使命感使我覺得,本來我沒有使命,但是這麼多人都死了,他們想要做的事,現在還沒有結果,我和他們不一樣,但是深層中是一樣的,我就希望中國好,我要有實際行動。遇羅克的這種勇敢,對我也有很大的鞭策。
我自己本來是一個文藝青年,喜歡寫詩、畫畫。定我們爲反革命集團還有一條,就是我們在一起成立寫詩的組織。當時,一有組織肯定就是反革命組織。我對於政治、道德勇氣,過去沒有這方面動力,也沒有這個要求,可以說遇羅克和跟遇羅克一樣的很多人,在這前後獻出了生命的人,對我說來是一種鞭策。並不是他們要求我這樣做,而是我覺得我們還有什麼更寶貴的?我們已經死過不止一次了。本來「六四」的時候我可以不管,可以不站出來,但是我覺得自己良心不安。就和後來一樣,我在海外寫一些文章,回來不斷地有麻煩、出事情,可是我自己覺得,如果我放棄自己的言論和思想,那我跟行屍走肉有什麼區別?我會想到遇羅克和與他一樣的人,他們活着會怎麼做?我雖然不是理想主義的先驅、同道人,但我是一個還能說話的人,我應該多說一點,就是這樣。
□ 根據「自由亞洲電臺」記者張敏採訪
轉自《華夏文摘》
(http://renminbao.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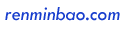











 打印機版
打印機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