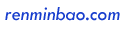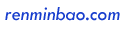|
【人民报消息】读了赵明的文章《从红朝谎言中觉醒》和司马泰的《一位大陆留学生心中的仇和恨》引起我的反思,我想我有必要把我成长中的一些经历与感受讲出来,进一步净化自己,同时以史为鉴,彻底看清中国、中华民族与共产党党的真实关系。 我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母都是五十年代毕业的大学生,他们颤颤惊惊活过了整个一生,但他们绝不承认他们是“顺民”,认为自己可以看透社会一切,因为我的爷爷和外公均是被共产党镇压了的,故他们认为自己能上了大学是党给予的极大恩赐,尽管历次运动他们都在劫难逃,但因为十分小心翼翼,叫作“夹起尾巴做人”,就没成为最吃亏的。最终他们认为自己很成功,不仅不心灰意冷,反而随著物质生活的提高,天天泡在电视、报纸(每天的功课),认为只有共产党才能把中国“敷”(统治)下去。其实他们物质生活的提高完全是因为儿女们承担了所有的费用,为他们买了房子、家具、电器,同时还有一大笔存款,常来美国转一转,他们的退休金变成了零花钱。而这一切的生活的变化,他们竟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共产党政策好了带来的。 我父亲几十年都是当的报纸编辑,应该对共产党造假那一套非常清楚,而我也认为自己的父亲差点被共产党逼得自杀,绝不会在关键时刻“倒”向共产党一边,“迫害”对他极尽孝道的女儿,可是我错了! 当他们第一次来美国,我们已是六年未见面了,大家还未在一起吃上第一顿饭(他们抵达是夜间),很自然就聊起了法轮功,因为那时我已在炼法轮功了,并且身心受益,我长久不治的胃病好了,而中国的镇压已有一年。没等我解释一句,没问我一声,我父亲便突然大怒,开始大骂法轮功,那架势似乎他有解不开的仇恨在里面,我太吃惊了,平时喜欢辩论的我此时完全傻了,没想到共产党天天造谣的一切,泼向法轮功的脏水,那些不堪一击的恶毒谎言,他吃得透透的,我完全始料不及,而我的任何解释他绝对一句也听不进去。 我只能一遍又一遍痛苦地问他:爸爸,你为什么宁愿相信共产党,对你有杀父之仇,对你剥夺了一切做人尊严(在过去几十年我父亲因出身问题被搞得不像人样)的共产党,而竟然不相信自己的女儿?你不相信,至少从人的角度,你也应该尊重别人的信仰吧?他这才停止了攻击与咆哮,但以后绝对不能听“法轮功”这个词,一听就跳起来。 有点不可思议,却是真的。几十年共产党用“无神论”洗脑,专制扭曲了一切人的心灵,人与人之间,一旦与自己的观点相悖,不是善意地去了解、包容,而是对立。表面上还是一个知书达理的人,但到关键时刻,良心、道义、正义、对与错、亲情全部都要让位于长期在不知不觉中被灌输的观念,从而随波逐流,甚至助纣为虐。 回过头来再说说我自己。我在修炼前也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有理性、能独立思考的人,读书时就不是那种安分守己的一类,在76年“四人帮”未打倒时,我曾被班主任打成“白专”生,甚至被全班批判,那时我刚读初二。我当教师的母亲也甚至认为我们这一代人的唯一出路是下农村,然后表现好了回城当个工人,甚至认为知识是危险的。而我那时只有十来岁,太渴望知识了,能支撑起我全部生命的就是想今后当一个科学家,所以我想发愤读书,在批林批孔时,批《三字经》,我读到那几句诸如“头悬梁,锥刺骨”给我极大鼓舞,我要说的这一切是想说明我自以为自己是一个清醒者。 有一个插曲是,当我于1979年初最后一年最后一学期准备高考时,中国向越南开战,其实是中国打越南,但我相信侵略者在冒犯我的祖国。记得那天老师正在给我们复习物理,我根本一句也听不进去,埋头给学校写决心书,我当时连团员还不是。写了一上午,头也未抬过,决心书中心是只要祖国需要,我宁愿放弃高考上前线。我真的当时是这么想的,要知道支撑我走过那么多生存磨难的最大希望是读大学,而我为了“祖国”竟在关键时刻可放弃读书,请绝对不要认为我是为了政治表现,那个时候人人在为高考奋斗,已是白热化,而政治已是一钱不值的1979年,我在班上的名声是政治上冷漠、自由化的那一小撮,但我真的对祖国有那么赤诚。 我在1979年十六岁时进了大学,正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最猖獗的时候,我利用大好时光博览群书,同时因为伤痕文学风行,我似乎也在看破红尘,对政治毫无兴趣,更是拒绝参加一切政治学习,结果成为系里要“挽救”的对象。一件偶然的事扭转了对我的处理,我有一位亲戚在美国,愿意帮助我移民美国读书,办理手续时当然都得通过学校。但后来因种种原因我的手续未办成功,而我当时也根本不想出国闯荡,此事就罢了。 三年以后,没想到学校竟通知报社(全市唯一的日报)来采访我,我不愿意,因为我不感兴趣那一切,然而学校和系里竟然软硬兼施非得让我接受党的“栽培”,我害怕毕业时不让我考研究生(那是我唯一的生活希望),也就在逼迫下极勉强地与一个记者谈了一下,没想到我竟被树成了典型,当然名声还不是那么难听:爱国。然而我明白这是当官的为了某种政治需要利用我而已,所以也还一副宠辱不惊的德行继续一心只读“圣贤书”。后来真凭本事读上了研究生,我可以沿著一条“科学家”的道路走下去了。 现在想来共产党成天宣传的“爱国”不是那么简单,首先,绝对是出于自身的需要比如有人要往上爬了。再有就是不断利用宣传一些真正的爱国知名人士为自己脸上贴金,还有一个用心就是用这种所谓爱国主义教育不断地给人民洗脑,诸如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如何受到列强侵略,中国人民如何生活在水深火热,清朝、白洋军阀、国民党如何腐败卖国,只有xx党是爱国的,所以是“共产党”救了中国。反复灌输宣传,共产党也就成了中国、中华民族的代名词了,只要反对共产党,那一定是背叛了中国,背叛了中华民族。这种教育天长日久,加上长期的歪曲、封锁一切真相,一切为其所用,最后会象毒汁一样浸入大脑,浸入血液,浸入骨髓。 我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我过去自以为已完全不在共产党教化的范畴之内,我敢说敢干,自以为很独立,对共产党的一切教条嗤之以鼻,敢辞职、辞职称、辞户口,在共产党的价值体系里我是一个绝对被排斥的对象,我也以为自己通过自己的头脑、观察及自己家庭成员的不幸可以认清其真面目,决不会为其所用。非也!身在其中,仅仅是中毒深浅的不同,甚至是不自觉地认同了而不自知。 我到了美国以后,变得非常爱国,这本来无可厚非,但这种状态有时会达到一种完全不讲理的程度。比如我在国内时也曾发过几句议论抨击腐败,但在美国一听到哪个人说同样的话我会变得非常愤怒,有几次和人争论,气得差点把车飞出高速公路,后来立下“条约”,开车时绝对“休谈国事”。这里说的“哪个人”还真不是什么“外人”,是我的先生(美国人),但在“爱国”问题上,即使先生也是“外人”了。我不能容忍外人对我的国家说三道四。一些变异的观念在我头脑里非常根深蒂固。比如:“家丑不可外扬”,“中国根本问题是老百姓的温饱,不是什么民主”。所以出国后我对共产党定义的“反华人士”很反感。有一个更极端的例子是:有一次偶然在报纸上看到有一个叫吴弘达的人要来我市,我当即怒从心起,决定要去会场让他难堪(当然后来没去),因为我仅凭一点隐隐约约的消息和感觉便断然决定吴是卖国!天啊,我现在想起都汗颜。 为什么我会这样,是因为我长期在那套谎言机制下被扭曲了,在变异的爱国主义情节下,已丧失是非判断能力,相信国家就是暴力机器,国家就是专政,不管共产党做得多么不对,它代表国家,代表中华民族,不管共产党多么惨无人道,说它不好就是给祖国丢脸。加上斗争哲学的熏染,对其一切不人道完全麻木。只要“爱国”,连好坏都能不管。可以说那个时候我的心是缺乏慈悲的,是干涸而缺乏温暖、扭曲的,尽管我从不敢做坏事或害人。 其实被共产党宣传的那些“卖国贼”,是一些忧国忧民的正义人士。就拿共产党的监狱来说,那里面有多少冤魂,而他们竟然在冤死时连器官也被掏去卖钱,饱中贪官的私囊,难道揭露了就是卖国吗?变态的专制把人从精神上剥夺一干二净,让人不相信来生,相信人死如灯灭,为的是更加有效地控制人的精神,动用一切专政手段随意宰割民众,人人不能幸免,人没有尊严。人与人之间无尊重、信任。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社会,其实中国老百姓的温饱,即使是在“腐败”的满清时代也不是问题,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的那一年,那时中国的国民生产总产值占世界的1/4,即25%,欧洲仅占世界的23%,现在中国是多少?7-8%,人口可是那时的10倍。新旧中国哪个行?不能光看共产党编的历史。 比如,江泽民自1994年6月26日到2001年7月17日与哈萨克、俄罗斯签订的一系列条约,总共出卖了中国14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面积超过四十个台湾,中国的国有资产,数千亿地被贪官私分、转移至外。真相被封锁了,共产党其实是这样“爱国”的。 而最广大的民众成了名符其实没有半点人格尊严的贱民,在国外的人都知道,比较其它一切国家的使领馆,只有中共这个使领馆对自己的人民是最不好的,我有一个朋友的姐姐结婚到了中东,哪知是被婚骗,护照被男人收走,嫁的人是有十几个老婆的虐待狂,生不如死,好容易偷跑到中国使馆请求保护,也就是说求补发一本护照,使馆坚拒门外,最后靠买了一本护照逃出魔窟。见死不救,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这样。 一个老年朋友告诉我,911那天,她正在中国城请重庆来探亲的亲家吃中饭,亲家是个退休的行长,看见电视现场直播有人从世贸大楼冲出窗户跳楼的惨剧,不仅不同情,反而说“好看,真痛快”! 为什么人会变成这样?长期变异宣传,煽动极端的“民族主义”,扭曲了人性,使善良的本性、良心被不善的、不道德的魔性取代,共产党能维持下去靠的是“斗”,把人性中不善的一面调动起来,从而在斗中渔利。即使它宣传的爱国也不是真正要把国家变成一个健康、法治、平等、幸福的社会,爱国只是一个被利用的幌子,为的是实行专制,而且利用人性的恶的一面,煽动起那种狭隘的无理性的暴力热情,转移社会矛盾和危机。从南斯拉 |